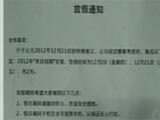“学长”杜耀强追忆郭建南。
——郭建南工友追忆与他共事的点点滴滴 朴实、热心、谦和的他令人难忘
文/记者蒋悦飞 图/记者乔军伟
就在去世前的那个月,他帮工友改论文改到了凌晨3点;
一声“师傅”,他对年龄相仿的陈志华叫了三十年;
明知做复杂的零件吃力不讨好,他却乐呵呵地毫无怨言;
当年朋友装修,他扛着几百斤的地板胶走了好几站路……
在工友的眼中,郭建南谦和忍让、技术高超,他让陈志华心怀歉意地说“下辈子我们不做师徒做兄弟”;他让一起穿着开裆裤长大的杜耀强发自内心地说“南哥,这一世我服你!”;他的匆匆而去,让工友们扼腕痛惜:如果他能不那么认真,他就不会那么早早离去……
“帮忙改论文改到3点,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
“凌晨3点多,当我从他手中接过修改过的论文时,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关耀章,郭建南30多年的老工友来了,他急迫地要向记者表达自己的谢意。
1980年4月,郭建南进厂,7个月后,关耀章也进了厂,两人都在同一个班组,30多年的情谊由此开始。而修改论文的事情发生在上个月月初的那个周末。那天,从阳西回来的郭建南在厂里碰到了关耀章。“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回家,在车上,我向他提起了正在评高级技师的事。”一直在生产第一线的关耀章不善文辞,对论文很头疼,想请老郭帮忙看看,因为下个周一,论文就要上交了。
“老郭说,那几天刚好是姨甥结婚,自己很忙,但是一定会抽出时间来看。”周六,关耀章将论文送给老郭,到了周日晚上老郭才闲下来,开始帮忙修改。
那一晚,显得特别长,“我在家里一直等,等到了(次日)凌晨2点半,实在等不及了,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再等半小时过来拿’。”3点多的时候,关耀章到了他家,郭建南果真已经修改好了文章。而8点钟,郭建南又得整装出发去阳西了。
“他说得到,就做得到。”关耀章表示。“想着他回来一起吃餐饭,都来不及了,我都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50多岁的关耀章,眼眶有点湿润。
“几百斤的地板胶,他扛了好几个公交站”
“前两个月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还开玩笑说我欠他一个人情,现在,叫我怎么还?”钟志强,郭建南的朋友、广重前工友来了,对老郭这份来不及的感谢,他将永远铭记。
1989年,钟志强大学毕业分配到广东轻工业机械有限公司,郭建南是团支部副书记,钟志强是委员,两人的交往非常密切。首先让钟志强打心眼里佩服的,是郭建南自强不息的精神。“老郭进厂的时候是普通工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那时,郭建南新婚不久,下了班之后就开始自学,先是学了广州市业余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接着又学北京师范学院金融专业。“拿到学历之后,老郭从车间调到了加工中心,这个中心有当年厂里最贵重的设备,而他是唯一的一个工人。”
由于老郭是鲜有的有实际操作能力又有理论知识的工人,不久就调到了技术组。技术人员最不愿意干的“粗活脏活”,老郭都不嫌弃。“他就是老黄牛。”钟志强表示。
老郭还特别热心,担任团支书的时候,有个姓李的工友的妈妈病了,他带头组织年轻人献血;一名姓杨的女工家里很困难,老郭带着团员去帮忙。
1992年,钟志强准备结婚,开始装修房子,那个年代装修都是自己搞,老郭又热心地忙活开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郭帮我去买地板胶。地板胶很重,市场又很远,上不了公交车。老郭和一个同事就一前一后,硬是把几百斤的地板胶从市场扛到了我家,有好几个公交站啊。”钟志强说,这件事情,也成为郭建南和钟志强之间最朴素最真挚的友情印记。
“我们要做兄弟不要做师徒”
陈志华是郭建南的师傅,移民国外已经十多年了,但是十多年来两人一直保持电话联系,讨论人生,讨论工作。听到郭建南出事,陈志华特别赶回了广州。对他来说,与郭建南相处的最大遗憾是:“我们要做兄弟,不要做师徒。”
“郭建南进厂的时候,是我学徒的第二年,实际上我的学徒期还没毕业,就带他当学徒,所以两个人年龄相仿,但是‘辈分是师徒’。”
两人相处的感情很好,一段时间后陈志华提出,“我们年龄差不多,我们叫‘兄弟’,不要叫‘师徒’。”“兄弟是兄弟,师徒是师徒。”郭建南表示。就这样,这一声“师傅”,一叫就叫了30多年,即便是陈志华离开了广重,这一声“师傅”还是会写在每年的圣诞贺卡上。
“贺卡上的祝福虽然很简单,但是每年都不会落下,一晃寄了十几年。”陈志华表示。
有一件事让陈志华记忆深刻并深感内疚。那时,师徒两人都调到了厂里的综合改革办公室,当时厂里的任务特别重,有大量的文件需要处理,正常下班时间是下午4:45,但办公室常常要在5:30开会。有一天下午5点,郭建南向师傅请假,说要去托儿所接一岁多的女儿。“当时我就批评他了,‘你为什么不叫家人去接?’”“就接一次,下不为例。”郭建南一个劲儿地道歉。
“事后我才知道那天郭建南的妈妈病了,他妻子又上夜班,家里实在没人。于是我问他‘为什么不解释?’郭建南回答说,‘谁叫你是我师傅?’我跟他都几十年了,根本都没有冲突的机会。主要是他迁就我、包容我。”陈志华说。
“不如我们帮他返工吧”
在工友的眼中,郭建南性格敦厚、随和,甚至是个“傻乎乎”的人,明知自己吃亏,还是乐呵呵的。在生产一线都是计件工资,所以大家都愿意挑一些简单的、容易操作的零件来做。但郭建南从来没二话,工友不愿意做的,他做,他的想法就是:“我们是年轻人,做复杂的零件可以学到更多的技术。”
让工友们念念不忘的,还有郭建南的一个小故事,“每次下班之前,他都会为下一班做好准备,把各种工装夹具收拾好。”这些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甚至还会影响他的产量,但是下一班工友来了,就不用费力收拾,直接干活就好了。就因为这,他的人缘非常好,跟谁都合得来。
陈志华还记得一件事,那时候他的对班(一个白班一个晚班)是专业军人,工作比较马虎,质检员对其印象不好。某一次,这位质检员来验收,问哪些产品是陈志华做的,哪些是他对班做的。由于两人的产品都混在一起不好分,于是质检员干脆说,对班的那一半都不及格。
这让陈志华很为难,苦无对策之际,郭建南说出了一句让他一辈子都记得的话:“不如我们帮他返工吧!”于是两人默默地帮工友把产品重做了一遍。
“他就是干得出这样的傻事,不会发火,有什么事都埋在心里。”陈志华说,“如果他可以不要那么认真,他就不会走。”
正是因为郭建南的这些品格,让广轻在向集团推荐扶贫干部的时候想到了郭建南。“扶贫工作很艰苦,要和当地的贫困户打交道,工作责任心要强,要有爱心,而郭建南一直乐于助人、任劳任怨,完全具备这些素质,所以我们就推荐了他。”广轻副书记梁鸿表示。“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答应了。”
“他一生不说大话”
杜耀强是郭建南少时的玩伴,也是同事,“因为他比我年长,所以我叫他‘南哥’,但在业余大学里我比他高一届,他就一直叫我‘学长’。”杜耀强表示,为了工作上的事,两个人时常会吵得面红耳赤,但是“每次我都会写一个‘服’字给他”。
2004年的冬天,特别冷。杜耀强和郭建南一起在组装一个啤酒灌装设备,价值几千万的设备,很复杂。当时杜耀强负责调试,郭建南是质检,也就是说最后是郭建南说了算。当时提出的技术标准有两个:一个是破瓶率要达到1%以下,一个是液面的误差范围在“±2毫米”。天冷手冻,影响了工作的精度,组装好了,但是两个技术指标都没达到。
“南哥,通融一下。”杜耀强撒娇了。
但郭建南却没松口,“咱们一起再看看。”后来两个人查到供货商提供的二氧化碳的截流剂有故障,换掉之后,液面的误差率达到了。而为了破瓶率达标,又把这套设备的120个瓶子全部拆下来,重新组装。
“南哥的技术很强大,总是在无声处感染到我们,让我们不得不跟随着他的步伐。”杜耀强表示。在工厂做ISO认证的时候,自己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郭建南也是简单一句话,“没问题,我帮你。”
“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我们多少都铜臭了,但是南哥是另类,还是个老实人。”杜耀强表示,“他一生不说大话,但这一世我就服他,怀念南哥,以后都会怀念他。”杜耀强有些情动。
广州好人
建德南粤
家庭传统教育铸就
郭建南“老实”品性
“郭建南有现在的事业,跟他家里的教养是分不开的。”退休工人陈柏芝告诉记者。
郭建南的爸爸郭威,是厂里的援外技术专家,在工人中非常有威信。“当年郭建南出生的时候,他正在援助越南建设,所以给儿子取名‘建南’。”
“他不但技术精湛,而且待人谦和有教养,分配到他爸爸那里去的年轻人,都很受益。” 陈柏芝表示,受郭威的影响,郭建南进厂之后都是任劳任怨、学习很快,一年之后就能承受复杂的零件加工,很少麻烦。有不懂的地方,也很虚心向师傅请教。“我当班长这么多年,他工作从来不挑。”
陈志华对郭威的印象也很深刻,“他在车间见到我,就当着他儿子的面叫我‘陈师傅’。当时我很尴尬,那时我才19岁,级别还是学徒,而他是‘老八级’。”但郭威却说,“师傅是不分年龄的。”
“他们一家都是很传统的,很有儒家风范。”陈志华说,郭建南的妈妈、弟弟、妹妹,每次见到他,都叫他“陈师傅”,一家人都很谦和。
记者手记
昔日慈父援建越南 今日孝子建德南粤
采访郭建南的事迹,记者前后与他的工友访谈了三次。第一次在广州市委,第二次在番禺广重办公室,第三次在石岗路的广轻。前两次,可能是因为场面太严肃,也可能是面对的媒体太多,看得出工友们有一箩筐的话,但是一句“他好好人”就结束了。于是,记者又约了第三次。
第三次,约在郭建南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广东轻工业机械有限公司。工厂有些破旧,办公室也很简陋,而工友们却都很淳朴、直率,这次来的人也特别多,有十几二十个。
“你干吗问得那么细,你只要写他乐于助人就很感动人了。”对于记者的“磨叽”,工友们刚开始并不接受。但当话匣子打开之后,他们开始主动说、抢着说当年和郭建南一起的点点滴滴,就在你一言我一语当中,慢慢地呈现出了郭建南活生生的形象。
采访中,他们一再地提到郭建南父亲郭威,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八级”深深地影响了郭建南的品性和技术,也感染着广轻的工友们。工友们特别提到,郭建南的名字就取自当年郭威“援建越南”,而如今郭建南在扶贫路上“建德南粤”。冥冥之中,父子两人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奏出了绚烂的华章。
(来源:广州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