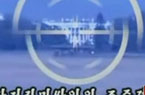刘德濒,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著名作家、编剧、导演。研究西藏历史、文化、民俗十数年,参与并创作《西藏风云》《回到拉萨》等涉藏作品多部,被公认为“西藏题材第一人”。 由刘德濒创作的小说《西藏秘密》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上图为刘德濒在拍摄《西藏秘密》电视剧的现场指导。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西藏秘密》这部小说以一个艺术家的视角,尽量客观地将一个真实的旧西藏展现给世人,试图在宽阔的历史时空中重现那段已经远去的岁月——农奴的悲惨生活和毫无人权;三大领主的剥削本性和奢侈糜烂生活;共产党解放西藏的英明和执行十七条协议的不折不扣。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彭雪婷
过去,刘德濒身上贴着“情感专家”的标签,《让爱作主》、《你在微笑,我却哭了》、《更年期的幸福生活》、《知情者》等代表作,所呈现的无一不是中国社会中家庭关系的情感巨变。然而,当他倾其十几年心血完成的长篇小说《西藏秘密》问世,且被他拍成电视剧在央视8套斩获超高收视与极佳口碑后,则又被誉为“西藏专家”。
可能是开学之初的缘故,身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的刘德濒课时排得满满当当。又逢《西藏秘密》小说发行期,约访不断。在历经“满档”的无奈后,我们的专访终于踩着截稿时间点匆匆完成。
谜一样的旧西藏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小说取名《西藏秘密》,“秘密”指的是什么?
刘德濒(以下简称刘):所谓秘密,一种是秘而不宣、被掩盖的;一种是被大家遗忘的。旧西藏的历史没有被掩盖,而是被歪曲。某些人故意否认一些重要历史真实的存在,故意否认西藏曾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另一种情形是,那段历史风貌更多地被善良的人们遗忘了,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学藏学的,如果不是14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接触到这片神秘的高原,我也不可能了解旧西藏。 1998年,因为参与中央电视台大型历史剧《西藏风云》的拍摄,我才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我惊讶地发现,我对中国西南的这个地方竟是如此高度无知,政教合一体制、十七条协议、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渗透、拉萨平叛战役等等,简直像谜一样。从此,我对西藏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非常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尤其是对1900年到1960年的历史作了全方位的认知,旧西藏在我的心目中,渐渐清晰起来,立体起来。抽象的概念变成了活生生的细节,奇异的表象变成了深刻的肌理。
我想,把我所了解的这一切告诉朋友们,大家一定有兴趣。比方说,1959年以前,谁是西藏真正的统治者,真是达赖喇嘛吗?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是怎样的?贵族是怎么生活的,农奴是怎么生存的?这些都是被当代人遗忘的秘密,是等待小说揭示的秘密。
记:西藏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都是神秘的,这与反映西藏历史的小说、影视作品较少有关。继《西藏风云》后,你又用十四年的时间啃下了《西藏秘密》这块硬骨头,为何对西藏题材如此热衷?
刘:我对西藏题材的热衷,除了西藏文化特有的魅力强烈的吸引我之外,也源于我自身的表达欲望。我想将我所了解到的旧西藏、我所热爱和钟情的西藏文化,用个人表达的方式进行一次诠释,应该说,这种诠释,不是历史学家的,而是一个艺术家的。不是官方的、正史的,而是一个个体研究者的。如果读者朋友们认为我的诠释是正确的,我很高兴。如果大家对我在小说中描绘的西藏产生质疑,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至少,《西藏秘密》给广大读者带来了一次“深度关注”西藏的机会。有关注,就会有了解,有了解,就会有认知,有认知,才更加接近真相,这是我的愿望。
记:《西藏秘密》后半部分所讲述的历史与《西藏风云》是重合的,十多年后再次来讲述这段历史,有什么不同?
刘:在时间上是重合的,从依托的历史脉络上也是重合的。这是真实的历史,不容篡改。但从艺术表现上,二者有很大的区别,《西藏风云》是历史电视剧,更准确地说是纪录片风格的历史电视剧。以正史表述为主,它的人物、事件、时间都准确到细部,是经得起推敲的。《西藏风云》纪实性是第一位的。后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叫《解放西藏史》。我看了,电视剧《西藏风云》与这本历史著作有着高度的吻合。
小说《西藏秘密》就不同了,我更强调它的艺术性,发挥小说艺术的虚构性特长。虽然还是依托那段历史,但那只是一个背景,是四个贵族家族故事发生的背景。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叫扎西顿珠的普通喇嘛,半被迫半自愿地充当一位贵族少爷替身的故事,这其中还包括几个小人物向往上层贵族生活的故事,一个不孝之子虚荣心膨胀、灵魂堕落的故事。所以,《西藏秘密》不是一部历史纪录片,更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一个艺术作品。
十年筹备查阅八米高文献
记:为了创作《西藏秘密》,你用了十年时间来准备素材。耗费如此长的时间?
刘:如今中国,艺术创作周期越来越短,尤其是影视创作已经形成了流水线式的快速生产模式。我的创作速度也很快。一般的情况下,一年会出一到两部作品。但《西藏秘密》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1999年完成《西藏风云》之后,我就一直想写这部小说,每年都在准备资料,准备动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年。我是一个在内地生活的汉族作者,想深入到西藏文化的内部、想到达它的细部,需要做纷繁复杂的功课。
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摞起来有八米多高,其中,包括一些国家的永久机密档案,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的档案。我走访了很多当年历史的见证人,有藏族,有汉族,有当年的贵族,也有农奴,还有十八军的老战士、老将军,这些准备工作为我完成《西藏秘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我希望小说《西藏秘密》是一部深刻的作品,是一部反思历史、审视宗教,甚至触碰某些敏感问题的作品。不躲避,不绕行,直视面对,这需要勇气,也需要等待时机。
我们知道2008年的春夏之际,在西藏拉萨发生了3·14事件,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件,震惊全球。3·14之后,国内的主流媒体对西藏的历史和西藏问题的由来,作了长达两个月的报道,之后又发生了奥运火炬受到境外藏独分子冲击的事情。这两件事,让我觉得创作《西藏秘密》的时候到了,不管从我个人的准备,还是从国家政策的允许,都是该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了。所以,从2008年9月份开始,我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小说,也完成了电视剧剧本的改编。之后,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拍摄并制作完成了电视剧《西藏秘密》。
记:除还原西藏的历史真实,还期望向受众传达一些什么思想?
刘:还有多少人对旧西藏历史原貌、社会风情、人权状况有深入、全面的、感性的了解?这是产生所谓的“西藏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西藏农奴制已经废除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国内外很多人、包括西藏本地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极少认知。忘记历史就无法走向未来。所以,我想通过《西藏秘密》这部小说来还原那段历史,以一个艺术家的视角,尽量客观地将一个真实的旧西藏展现给世人,我试图在宽阔的历史时空中重现那段已经远去的岁月——农奴的悲惨生活和毫无人权;三大领主的剥削本性和奢侈糜烂生活;共产党解放西藏的英明和执行十七条协议的不折不扣。牢记历史,才能走向未来,才能找到民族的根。
勇闯望而生畏的“雷区”
记:你的作品直面西藏历史中最为严峻而又敏感的政教合一问题,如果讨巧一些只是从西藏的风土人情来入手也不是不可,为什么偏要迎难而上呢?
刘:这跟我个人的秉性有关。我可以很坦白地说,如果仅从风土人情入手,对藏地文化和民族风情抱有某种猎奇的态度,我就没必要写这部小说了,更不值得我花十几年的时间完成这个项目。正是因为它敏感,别人不敢做,不敢碰,我才想动它一下,这才是你的说“讨巧”。
因为这个题材和角度的作品极度稀缺,读者才更有兴趣读你的小说。我拿到样书的时候,看见出版社在腰封上有一句广告语:“首部深度透视西藏神秘文化和历史真相的史诗巨制”,“从来没有一部小说,能像《西藏秘密》一样,以讲故事的方式对西藏予以详实、清晰、大胆地披露,不仅向读者全面呈现藏地的神秘文化、风土人情和政治变迁,还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了解西藏历史真相的渴望。”这是编辑的感受,我想,也将会是读者的感受。
对于读者来说,通过一些文艺作品,他们似乎了解了西藏。从电影《农奴》中,他们知道了旧西藏受欺凌的农奴;从小说《尘埃落定》中,他们知道了川西土司的历史变迁;从电视剧《西藏风云》中,他们知道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从《康定情歌》、《茶马古道》中,他们知道了四川和云南驮帮的传奇故事。从美国电影《西藏七年》、《昆顿》中,他们看到了西方人眼中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西藏僧侣贵族生活。
但我告诉大家,这些作品中缺少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西藏以拉萨为中心的上层贵族生活,也就是“三大领主”中级别最高的那个层次的人的生活,在西藏他们才是真正的“人上人”。他们是政教合一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决定了西藏历史发展的方向。不了解他们,也就无法真正了解西藏社会的本质和西藏问题的来由。这是小说《西藏秘密》的价值所在。
记:这也是选择站在极少数的大贵族阶层的视角上来揭开这段历史的原因?
刘:是的,称其为阶层,其实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据权威藏学家调查统计,我在小说中所反映的那个年代,这些顶层的贵族,全藏只有175家,分住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这些上层贵族,因为在文艺作品中极少被提到,所以非常神秘,极大地刺激了读者和观众的求知欲。
贯穿西藏现当代史的“红线”
记:《西藏秘密》所呈现的旧西藏的“顽疾”与今天的西藏问题有没有什么历史关联?
刘:1959年以前的西藏社会是一个阶层分化极其严重的畸形社会,等级制度严格而残酷。以贵族,噶厦政府的高级官员和高级僧侣集团为首的三大领主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拥有对土地、农奴的支配权,对占人口95%的普通农奴阶层进行盘剥和压迫。农奴们要付出沉重的劳役,没有人身自由,可以随便被处置、被出卖。电视剧播出后,有一位内地的普通网友@伍德兄发微博说:“西藏问题根本不是民族矛盾问题,而是旧奴隶主贵族想复辟。”我觉得他说得很精辟,一针见血。
记:小说中,无论是大贵族、中小贵族、喇嘛还是农奴,都有那么一部分人始终坚定不移地反对藏独,这是不是真实的呈现?
刘:在西藏现当代历史上,有一条粗粗的红线贯穿始终,那就是,曾有过一大批各阶层的藏族同胞坚定不移地反对藏独分裂势力,维护了祖国统一的爱国线。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摄政王热振活佛一直心向内地,情系祖国,和中央政府始终站在一起,维护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为和平召开法会,祈祷抗战胜利。在东部沿海被侵华日军封锁以后,西藏的爱国人士不顾噶厦政府的阻挠,在青藏高原上,在祖国的大西南,建立了一条支援抗战的交通线。邦达仓、热振仓等上千支商队将大批生活物资和盟国的军事物资运往内地,打破了日军的经济封锁,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又有像阿沛·阿旺晋美、德木活佛等众多的爱国人士,不惧分裂势力的阻挠甚至迫害,主动卖粮食、卖房屋给解放军,帮助进藏部队解决吃住问题,在西藏站稳脚跟。当分裂分子发动骚乱和叛乱的时候,从农奴、中小贵族、喇嘛,一直到上层大贵族,不同阶层的爱国人士主动给解放军送情报,传递信息,保护政府机关,甚至同分裂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抗争……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至今让人感动。
记:这些思想进步的西藏大贵族,也有谋求政治革新的愿望?
刘:是的,在小说中也有呈现。以主人公扎西顿珠为代表的西藏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西藏社会的愚昧与落后,他们强烈地提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要求。扎西顿珠个人的核心思想是佛教的“普渡众生”的理念,他在印度游学的时候,将这一思想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了揉和,觉得这才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普渡观,是拯救西藏众生的良方。但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主张只得到了少数上层人士的支持,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扎西顿珠与共产党、解放军相互理解、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他们从共产党人那里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穷威力,也最终找到了指引西藏社会走向现代、光明、真正幸福的道路。正因为如此,这些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并彻底推翻了西藏千百年来的农奴制度,使西藏获得了新生。百万农奴翻身,这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普渡众生出苦海的伟大实践。
记:《西藏秘密》在央视8套播出时的收视率很高,听说在拉萨有很多人都在追看这个片子,有没有得到来自藏区的反馈?
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研究员次仁央宗是拉萨人,也是当年的贵族出身。他说,《西藏秘密》播出以后让他很欣慰,他能在片子里找出家庭或人物的历史影子。他曾研究过拉鲁家族,但从来没敢想把它弄成一个艺术作品,因为这个题材是非常不好把握的。现在看到《西藏秘密》表现的是旧贵族生活,让他很感动。
(来源:大众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