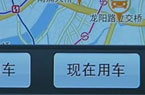湖北日报讯 图为:冬天的涨渡湖湿地。
图为:红嘴鸥
图为:欢快戏水。
图为:鸟儿在涨渡湖湿地繁衍后代。
图为:涨渡湖湿地杉树上栖息着无数鸟儿。
图为:夕阳下的鹭鸟。
林业部门的护鸟员在湿地观察鸟儿生活情况。
记者 易建新 通讯员 程书雄
涨渡湖位于东经114°41’53"北纬30°38’23"
面积
涨渡湖水面面积35.8平方公里
红嘴鸥种群全国罕见全省第一
“看一个地方生态好不好,就看鸟来多少。”
——赵学敏(原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没有围网,没有竹竿,没有渔舫,眼前终于出现了烟波浩渺的万顷波涛。
跑了不少湖,我的视线总被密匝匝的围网遮挡,被一条条的湖堤厢埂隔断。我想象中的“湖光山色”没有出现,目光所及,往往只是凌乱的切片,风景只在久远的记忆里。
新洲,涨渡湖,终于让我的视线无限伸展,辽阔水面的那头,仿佛湖与天接,万顷波涛成为天幕这一巨幅油画的背景,悠远深邃。
3月10日,虽有丝丝早春的寒意,但涨渡湖春天的脚步似乎来得更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行进中,湖边夹岸的油菜花沿途开满春天的芬芳,如缀在涨渡湖的条条金黄色缎带。粉红色的红叶李,则在涨渡湖的入口上,随风轻飏,似在招手: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请你留下来,在涨渡湖听鸟。
美国“鸟人”的“假钱”
在涨渡湖,经常有一些爱鸟者前来观鸟,其中不乏国际友人。他们自带干粮、帐篷和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在涨渡湖住下来,时间有长有短,短则几天,长则数月。业内习惯称这些发烧友为“鸟人”。
2009年12月23日,天气寒冷,一美国教授,长得人高马大,为了近处观鸟,找当地一老农借过胸水衣下湖蹚行,一不小心,水衣被水下荆棘刺破,遍体进水。上岸后教授到老农家火炉旁烘烤良久才干。教授拿出100美元给老农赔水衣钱,老农不认识美元,以为是假钱,不收。后来通过翻译,换成了人民币,老农才收下。
神奇教授船上听鸟
涨渡湖究竟有多少种鸟?杨其仁教授光凭一双神奇的耳朵就能听出来。
1995年6月,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其仁(现已退休),来到涨渡湖。
时值炎夏,杨教授找当地渔民租一小船,自己慢慢划到湖中。教授静坐于湖中一隅,在离鸟最近处,双目微合,心安神定,虽然要忍受身旁之蛀虫、头顶之烈日,却有阵阵天籁之音从湖的各个角落传来,时高、时低、时长、时短,如多声部的合奏,抑扬顿挫。教授如欣赏一场专门为自己举行的专场音乐会,如醉如痴。
3天听下来,杨其仁准确地分辨出,那年夏天涨渡湖的鸟,有37种。新洲区林业局副书记胡长发说:“涨渡湖鸟的品种,都是杨教授听出来的。”
据介绍,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武汉大学、中科院水生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多次来此实地调查。目前,涨渡湖已确定的鸟类103种,水体原生动物达11种,水体浮游甲壳类动物6种,两栖类动物10种,爬行类动物16种,哺乳动物20种。
涨渡湖也成为本地科普教学最好的实地。每年,武汉大学胡鸿兴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刘胜祥教授、湖北大学汪正祥教授及武汉观鸟会的老师们,都要带几百个学生到涨渡湖来观摩教学。
尼克松带来“大屁股树”种子
到涨渡湖湿地,有一种水中的树特别引人注目。其高达25米左右,主干挺直,树干基部膨大,枝条向上形成狭窄的树冠,呈尖塔形,状如罗汉。这种树学名叫“池杉”,因出水部分瘦劲挺拔,根部沉水部分肥大,当地老百姓习惯称为“大屁股树”。
专家介绍,一般的水杉生长在岸上,长年沉水根本存活不了。池杉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其“大屁股”——部分根垂直向上伸出土面,暴露于空气之中,便于进行呼吸。
新洲区林业局有关负责人透露,此树原产于美国弗吉尼亚,种子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赠送的。中国自上世纪初,引种到江苏盐城及鸡公山和大丰杉木基地等地方,后引到杭州、武汉、庐山、广州等地。涨渡湖1974年栽种此树。
10万红嘴鸥铺上红毯
冬日来涨渡湖,你肯定会不虚此行。一定要带好相机,抓拍这最温暖最动人的画面——近10万只红嘴鸥,如红色的锦缎,铺满整个湖面。
新洲区水务局局长王华林说,一到冬天,涨渡湖50公里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红嘴鸥舞动的倩影。她们白天出去觅食,晚上回“家”休息。“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些晚归的鸟儿,还找不到地方住。”
可以想像那场面多么壮观,那情景多么生动。生活在涨渡湖边的人们多么幸福,他们的冬天一定不会感到寒冷,这大片红色火焰,让他们感到无比温暖。
好景人乐 好水鸟栖
鸟择水而居,对水质有极高的要求,是湖泊生态最公正的裁判。
涨渡湖为我们打开一道新的风景,值得总结,也让记者陷入思考。涨渡湖生态保护工作虽然不尽完美,留下一些遗憾,但和全省其他湖泊比起来,似乎很有推介的必要。
1.隔断、改道两水,为涨渡湖减负。
涨渡湖因“涨水为渡,落水为湖”而得名,远古时为云梦古泽,彼时与长江相通,南受长江倒灌,北纳举水、倒水流域6371平方公里的来水,入湖水量达到30亿立方米,素有“汛期一湖水,枯水一片荒”的说法。1840年至1850年10年间,曾连续发生11次水灾,其中大灾5次。1953年春,长江水利委员会兴建涨渡湖蓄洪垦殖工程,隔断了举水。但从1949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有关方面对倒水进行过多次治理,但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解决倒水冲击的契机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资料显示,那个时候,新洲是全国有名的产棉区。倒水的泛滥,往往使棉产区受灾严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1970年2月,周恩来总理下达了“苦战两年,解决倒水问题”的指示。在李先念副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倒水改道工程顺利进行。至1973年,主体工程完工,终于将倒水1793平方公里来水全部撇入长江。
此一工程,为涨渡湖生态修复水质稳定,提供了先决条件。
2.让专业渔民尽早上岸。
与前者比起来,这项属地方性可控性工作,看起来小,其实最难。记者在洪湖、龙感湖等湖采访,各方谈到湖泊生态保护与管理最难的环节是人——长期以湖为生、没有土地的专业渔民,他们吃喝拉撒睡都在湖里。而这些大湖上的专业渔民,往往有上千人。
让他们上岸困难多多。一要买下他们的生活用船;二要让他们离湖后有地方住,给他们建房;三是如果不让他们再当渔民,还要买下他们的工作用船(打鱼船),给他们安排新的工作。后面的问题接踵而来:孩子上学、就业、工作、成家……这是让管理部门一提起就头大的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政府投入之巨,无法估算;民间资本介入,也有很多困难。
但涨渡湖做到了,这才有记者开篇见到的令人欣慰的场景。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涨渡湖就让所有的渔民上岸,通过治理倒水湖,浅湖造田,把其分给没有土地的专业渔民。虽然有关方面对投入之大没有透露,但可以想见。其工作之繁,更不必赘述。
涨渡湖浅湖造田分给专业渔民,其经验也许不能复制,但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思路和启迪。
3.“湖长”负责,既有多头,更有集中。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湖泊保护实行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根据武汉市湖泊管理的要求,涨渡湖由区政府领导任“湖长”,对湖泊保护管理实行总负责、总协调。
好处多多。环保、旅游、城建、规划、土地、水务等多头管理扯皮拉筋的事,最后在“湖长”那里一锤定音。以记者采访所见,湖泊管理最复杂的问题往往是多头管理中,大家同一级别,互不买账。以某湖为例,湖中的农场和湖管局属同一行政级别,都是正处级,关系比较微妙,管理难度可想而知。还有最难的,是跨行政区域的管理,如洪湖,涉及洪湖市与监利县;斧头湖涉及咸宁与武汉;更难的是,龙感湖跨省,涉及湖北与安徽。
涨渡湖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不仅如此,涨渡湖边的临湖村组每小组固定一名同志,称为“草根湖长”,划定责任范围,各负其责。
涨渡湖在这几个关键的问题上,抓住了契机和要害,控制了大局。相对其他而言,无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然而,这背后的难度和付出,也相当之大。
传说·故事
包公照妖镜
传说包公从黄州到定远上任时经过此湖。时为午后,艄公对包公说,午后过不得涨渡湖,有出水妖怪。船行湖中,果然出现一怪物,兴风作浪,包公站立船头,手拿照妖镜大吼:“妖怪们,试试我的厉害!”妖怪吓得逃走。包公离开时将镜送给艄公,不想重有千斤,艄公失手,镜碎于湖中。现此处流行:“包公到,百姓笑,湖水当着镜子照”。
李时珍煎药
有一天,李时珍采草药来到此湖,看到一老人痛得在地上打滚,李时珍赶紧解开随身带的小锅,用三个指头按住菇子为老人煎药。可药煎好后,老人却不见了。李时珍把锅里的菇子连水一起倒入涨渡湖,引来一群黄颡抢着吃。李氏的善良和医术从此传遍江湖。
历史钩沉
红色之湖
涨渡湖也是一座英雄的湖。涨渡湖抗日根据地曾经威震八方。有多少英雄好汉,在涨渡湖的刀光剑影中脱颖而出,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栋梁(按时间先后):
文祥:黄冈中心县委书记、独立游击5大队政训处主任、鄂东地委宣传部长;
漆少川:独立游击5大队3营营长、新四军5师14旅41团团长、第4军分区黄冈指挥部指挥长;
张体学:独立游击5大队大队长、新四军5师14旅政委、第5军分区司令员;(此3人为涨渡湖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者)
李先念:时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鄂豫边区党委书记;
陈少敏:时任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新四军5师副政委;
刘西尧:黄冈中心县委书记、独立游击5大队军政委员会书记、5军分区政委、长江地委书记;
方毅:鄂东特委副书记、独立游击5大队军政委员会书记;
林少南:新四军5师14旅40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第4军分区组织干事、第5军分区政治部机关指导员;
王群:新四军5师13旅宣传干事、组织干事、指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设立的相关机构旧址
财税所、14旅野战医院、洪公学校分部、鄂豫边区建设银行第三印钞厂、勤务科、修械所、织布厂、被服厂。
(新洲区文史办提供)
本版摄影记者 曲河本报视界网邱新明 肖劲松
(来源:湖北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