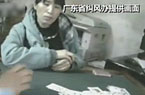非典患者方渤
中广网北京4月17日消息(记者王娴 刘黎)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那个春天给了一些人特别的身份,“非典病人”。多数人后来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少数人日子被定格在了非典里。
这十年,有人开辟了新的人生,也有人还在挣扎着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里,都努力想要更好的生活。
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精神抑郁,这是走不出非典的人群共同的境遇。时隔十年,他们有什么诉求,又有哪些待解的难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非典,十年回首》今天播出第二篇《为了更好的生活》。
边晓春说,自己是非典患者中的“非典型”,非典治愈后,一直正常工作,最近才从北京一家芯片设计公司退休;非典治愈后,因大剂量使用激素患上股骨头坏死,7年中药治疗,竟然痊愈,可能是北京非典患者中,股骨头坏死病愈的唯一病例。虽说股骨头坏死有极低的自愈率,连医生都惊讶边晓春能成为难得的幸运者。
边晓春:他仔细看我的那个CT,拿出自己的照相机照,他说你真是好,从骨头的那个状态上来看,和平常人已经一样了,但是那个病灶在,核磁共振能把那个病灶照出来,那个病灶的钙化大概是要20年左右的时间,病灶的存在并没有影响我的股骨头里面的这些的骨小梁正常的新陈代谢。
采访多位非典患者,边晓春是最自信也最理性的一个。这位金丝边眼镜,格子衬衣的男士讲话从容,极有逻辑。也因为这个特点,他是北京非典患者圈子里“智囊团”的核心之一。十年前的4月11日,边晓春送家人去人民医院看病,之后低烧,被确诊为非典;十年中,先是去青岛散心度假发现腿疼,回北京医生就判定股骨头坏死,告诉他“等着置换关节吧”。十年后,身体康复,有关非典的思考随着经历的累积,而愈发清晰。都把非典评价为公共卫生事件的里程碑,边晓春的体会更为直接。
边晓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是一个卫生事件,它是一个社会事件,让公众知道这个事的真情是政府的责任。非典以后政府对于社会民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出台了像公共卫生事件法这样的重要条例,并且重新组建了中国CDC的整个一套体系,使得我们国家在面对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增长,社会公众对于这种事件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北京,因非典而患上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抑郁症等疾病的患者有个上百人的圈子,边晓春也因此结识了更多的同命相怜者。他总说,自己是个特例,身体好了,经济条件也不错,常和病友们一起,哪怕听他们讲讲最近是不是又住院了,关节疼痛有没有缓解,谁家有困难时,搭把援手,都是在相互分担。其实,大家聚在一起,更多的话题还是将来。股骨头坏死,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残疾证,身体怎么办,养老怎么办,这些问题,很现实。大家的诉求很集中,希望得到更多的救助与关注。边晓春说,这些困难虽然和他个人无关,但他还是要替同伴们说。
边晓春:这种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出来了以后的这些受害者,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给予救助?主要是亡故者的家属、致残者本人及其家属。救助到底从法理上应该循一个什么样的法,从资金来源上应该组织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救助架构,从怎么去调动社会的其他资源,譬如说志愿者等等的,给这些人更多的及时的关照。
这些仍被非典困扰着的病人慢慢聚在了一起,有的是在病房里相识,有的是在检查身体时偶遇。病友成了他们最亲切的称呼。和病友在一起心里才踏实,因为同命相怜。
十年,他们的生活轨迹因为非典而改变,十年,虽然一直在和身体,和生活做抗争,经历的同时,他们更在思考。
方渤应该算是非典患者中的“名人”,见到他是在广州,他从北京去广州的一个目的,是想见见钟南山。听方渤说他的非典故事,他总是提起2003年4月8日卫生部下发的84号文件,把非典定为法定传染病。
方渤:2010年年底,我们有个朋友在网上突然发现,2003年4月8日卫生部根据国务院会议精神发了一个84号文件,84号文件就明确说了,根据国务院会议精神,把非典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我们当时就跟抓到一根稻草似的,我们发病都在2003年的4月中旬以后,你像我们家是4月16日。
这份文件,边晓春也挂在嘴边,除此之外,2006年颁布的《公共卫生事件法》也被他们反复引用。边晓春说,救助的前提在于非典究竟是突如其来的天灾,还是一种传染病。大家寻找的只是救助的法理依据。
边晓春:我们从来无意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我们只是要找到一个法理根据,依法对这些人进行救助。
上个月,方渤去八达岭人民公墓给亡妻扫墓,这是他10年来第二次看望因非典而去世的妻子。家里9人感染非典,两人去世,包括自己在内的多位亲属被查出股骨头坏死。如今的方渤,悲观易怒,甚至有些抑郁。每隔半个月,这些患有股骨头坏死的病人都会去趟北京望京医院,拿药、按摩,医院对他们有专门的绿色通道,方渤说,这么多年,他和关节三科的医生们很熟。对这个群体来说,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精神抑郁是目前三类可以报销治疗费用的疾病。
方渤:有工作的给补助4000,没工作的,给补助8000。我们希望给我们增加三个中医院,就给我们增加了三个中医院,希望能增加心理干预治疗,又给我们增加三个心理方面的医院。
广州简陋的小旅馆里,方渤让记者看照片、看视频,这都是他搜集的非典同伴的生活境遇。和方渤同去广州的,还有一位比他年轻很多的女士,俩人穿着玫红色情侣短袖,方渤要提供资料给记者,总要先问问她,东西在哪里。送记者出门时,方渤小声说,“她一定要在身边照顾我,真怕耽误了她。”多种疾病缠身,已是花甲之年,方渤不能不担心将来。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等不起。
方渤:社会劳动保障局给我们鉴定,我们没有劳动能力,北京市残联给我们鉴定我们没有生活自理能力,更多活儿我们不能干,我们不能负重,而且我们活动受限,我这一躺在床上,我05年半年躺在床上,我连轮椅都坐不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人等不及了,我们现在有瘫在床上的,有得癌症晚期的,还有四个已经去世的,他们今天的后果,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明天。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方渤、边晓春就在忙活儿一件事儿,创办专项救助基金。有家企业愿意捐款,一个月出三万块钱。这项捐助最终成了北京市残联下属的残疾人基金会的项目。虽然钱不多,却是盼望多年后的新起点。
方渤:就从200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香港有个基金以后,我们就特别希望北京也能有个基金,我还是希望有这么个东西能帮下我们,让他们虽然说过得不太好,但是可以稍微少一些痛苦,心里多一些平衡。
一个月3万块钱。怎么分?家庭情况不同,病情也有轻有重,边晓春提出了加权平均法。领钱还得打分,残疾人算一分,重残算两分,家庭有非典亡故者,加两分。一个季度领一次钱,80多个人受益。遗憾的是,因为挂靠残联,比如非典治愈后,肺纤维化的患者不是残疾人,即便生活困难也享受不到这份救助。在边晓春看来,重要的是“先把池子建起来”。
边晓春:我们一直在呼吁建立一个基金,或者在某个法定基金会里的一个项目来收集社会上的各种善款,包括政府的善款对于这些非典受害者进行救助。
方渤觉得,十年像一天。他们从原来的生活中甩出,定格在2003年春天。边晓春的思考更在当下,十年,该是个节点。他认为该用一份客观的调查回望2003,记录他们的十年。
边晓春:这种回顾性的调查是以总结经验教训为目的的,包括疾病控制界、医疗界、科研界、这些非典受害者以及社会公众和相关的这些政府里面的卫生部门的官员,都应该是被调查对象,应该有一个全方位的、认真的对非典的一个回顾。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时候,对于非典当时的一些前因后果、处置以及善后做一个非常全面、多方位的调查,这件事此其时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新闻热线4008000088,拨打热线电话即可将您手中的新闻线索第一时间反馈。我们将第一时间派出记者调查事件、报道事实、揭开真相。)
(来源:中广网)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回访和习近平握手渔民
回访和习近平握手渔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