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名作《蝶恋花·春景》赏析札记
徐海清

▲苏轼墨迹

苏轼赏竹图
◆徐海清
前不久,文汇报记者在报道筹建中的上海电影博物馆时,提及中国电影史上东方“诗电影”代表人物费穆和他执导的影片《小城之春》。据说,费穆这部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按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也作《蝶恋花·春景》)词意境和韵致构思全片视听形象的,他把这部讲述家庭情感波澜的影片拍得充满诗意;“词境中的哀怨感伤,黯淡怅惘,化为电影的淡墨山水小品,苦涩的茉莉香片”。且看苏东坡这首名作: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一直以来都被选家作为苏东坡的代表作收录各种选本,但注释和串讲、点评、赏析文字则有不同之处。主要分歧是:一,此词作于何时何地?不少学者认为是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前后,苏轼被贬惠州期间所作。鉴于此说所据宋人笔记相关记载真伪难辨,因此又有更谨慎的说法是,“此词作于何时已不可考”或尚待详考。二,对作品不是写一般的儿女之情没异议,但究竟“寄托”了什么样的情绪,说法不尽一致——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仕途坎坷、飘泊天涯的失落,也即费穆当年所感受到的“哀怨感伤,黯淡怅惘”;2.伤感中蕴含着随遇而安的旷达,以至所谓“无往而不适”的旷达。
笔者以为,“即使苏轼这首词不是作于惠州,也颇能代表他们(苏轼及其伴侣朝云)贬官惠州时的心情”一说(参见唐圭章主编:《唐宋词鉴赏》中曾枣庄的赏析文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应该是站得住脚的;本文不拟探究作品创作年代,仅讨论“心情”问题,即这首《蝶恋花·春景》“寄托”了苏轼什么样的情绪?
一,“天涯芳草”是递进不是转折
在所谓“寄托”问题上见解不尽相同的原因,从文本看,首先在于对词中“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理解各异。
词学家胡云翼的《宋词选》对这一句的注释是:“芳草长到了天边,表明春天快完结了。”王水照的《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作“谓春光已晚,芳草长遍天涯”,与胡注相同。这就是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句是在“花褪残红青杏小”、“枝上柳绵吹又少”基础上的一种递进——继续抒发伤春之情。这首词上片伤春,下片伤情,作品“感慨美景不常,繁华易逝,可谓一气贯注。”(曾枣庄语)胡云翼先生在他选注的《唐宋词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中,苏轼这首《蝶恋花》的注者“说明”为:“诗人关心春景,可是目前到处落花飞絮,一年的好景致又过掉了。诗人喜爱佳人,可是墙里的佳人不理睬他。前段写景是实写;后段抒情,是虚写,是借偶然见到的情事来表达‘墙外行人’失意、寂寞的心情。”短短不满百字,把词的意思和写作特点讲得一清二楚。
有论者指出:“枝上柳绵吹又少”一句,描述了人生的无常,“天涯”一句,化用屈原《离骚》中的诗意表达人生普遍之意,两句词形象地表明,人生无常本就是不可违抗的自然原则……(康震:《康震评说苏东坡》,中华书局,2008年1月)此说也值得体味。
有些选本或论著的解释就大相径庭了,如:
“春草原是春的使者,并随着春的足迹走遍天涯。而它却不似春花的娇弱,不怕风雨的吹打,它随春而来却不随春而去。”(黄润苏王文鹏:《婉约词选一百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
“天涯何处无芳草”被当成了转折句——春天将逝,但也无妨:尽管已是暮春,但还有芳草绿遍天涯。于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就被认为营造了“另一种意境……难道就看不见任何生气吗?”“当诗人对着“花褪残红”或感叹暮春时,却顿然以菁菁芳草的绿遍天涯而感到一种欣慰”。
类似的表述又如:“柳絮虽飘落殆尽,芳草却遍布天涯,‘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结句又以乐观开朗的情绪化解了这种悲哀。”(见《宋词画谱》中綦维的注释。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5月)
更有甚者,称:“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刻画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晚春图。特别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更进一步抒发了自己“无往而不适”的旷达胸怀。(李华编著:《宋词三百首详注》,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5年10月)
笔者以为,如果把“天涯”句解释作者的情绪在此发生了转折,由伤感变为“旷达”,或者是“伤感中蕴含着旷达”,甚至说“体现了诗人以退待进,处逆不惊的博大胸襟”。那么,就与下片“墙外行人”的失意心境上下之间断了气。“处逆不惊的博大胸襟”云云,应该不是东坡本意。
二,“豪放派”词人也会有哀怨时
一些论者把《蝶恋花·春景》寄托的“旷达”情绪推向极致的原因,除了对文本理解的不同外,还因为他们从作者的性格、人生态度和他们认定的苏词风格出发,把一个在特定时期、环境中产生的作品安置在总体意义上的个性、词风的框框里来理解了。
他们认为:苏轼一生虽积极入世,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老庄及佛家思想影响颇深,每当由于政见不同或权力之争而导致官场失意、处境艰难时,他总能“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表现出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洒脱情怀。与这一观点相关的另一个说法是:作为一个“豪放派”大家,苏轼的婉约词也同样有劲气流动,不同于“婉约派”的软弱。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文学史的编撰者、词论界普遍认为宋词有婉约、豪放两个流派。“以苏轼与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被视为宋词的“主流”。“豪放派”常常被过分抬高,“婉约派”则每每遭任意贬低。词人一旦被戴上“豪放派”桂冠,就容不得他有不“豪放”的情绪;即便是在他的“婉约词”里边,也要找出点与“婉约派”不同的“豪放”意味来,好像不这样就会有损“豪放派”形象。
有关宋词“婉约”、“豪放”两个流派的一系列传统的“主流”看法,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其中吴世昌的观点相当突出。吴先生说:“凡强分宋词为‘豪放’、‘婉约’两派者,乃欲放婉约之‘郑声’,定宋词于‘豪放’之一尊耳。无奈北宋无此豪放一派耳。”“世称东坡、稼轩为豪放词派,然东坡乐府三百四十首中豪放之作……不过三五首耳,他的词多属‘婉约’一派……曰东坡为豪放之主,真自欺欺人之谈。”吴先生还指出,东坡之“豪放”,“乃指其人性格,非指其词作风。坡词多小令,岂能‘豪放’?”(吴世昌:《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2000年2月)笔者以为,分宋词为“婉约”、“豪放”两派,特别是高抬“豪放派”、贬低“婉约派”的观点在上世纪的流行,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今人不宜苛责,但指出其不妥之处确实十分必要。
如果一成不变地用“豪放”或“婉约”的概念来界定苏词的风格,就难以准确厘清和理解苏轼随着身世、处境的变化,其精神状态发生相应变化的轨迹了。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涉嫌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罪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后,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检校水部员外郎,职位低微,且无实权。但苏轼在黄州期间,曾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以此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它们都被认为苏轼豪放飘逸的巅峰之作。另如元丰五年(1082),即苏轼贬谪黄州后第三年春天所写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云: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者不难从这首文辞清新的作品中,体会到作者无所谓“雨”“晴”(喻逆境和顺境)的平常心和豪迈情。3年后,即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驾崩,哲宗登基,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新党遭打压,旧党获重用。从是年五月以后的17个月里,苏轼从朝奉郎知登州(官阶七品),一路升迁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三品),速度之快完全出乎人们包括他自己的想象。然而不久,苏轼又处于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的境地。元祐四年(1089),他再度要求外调,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知杭州。元祐六年(1091)春,还在知杭州任上的苏轼,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途经杭州的老友钱穆父,写下《临江仙·送钱穆父》,其下片云: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轼感到钱穆父的命运与自己有相似之处。与当年那首《定风波》相比,作品在旷达之语的背后,对仕宦浮沉的惆怅,以及对身世飘零的慨叹已流露得十分明显。
同年,苏轼被召回朝。但不久就因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今安徽阜阳)。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得势,第二年,即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六月,苏轼被贬为宁远军(今广西容县)节度副使(正职也只有从八品,如果是贬降官,只给半薪);不久,被再贬至岭南惠州。
从元丰五年(1082)到绍圣元年(1094)十余年间,苏轼仕途荣辱沉浮,其中一段日子像在政治游戏场里坐“过山车”,最终一落再落。假定《蝶恋花·春景》确是作于绍圣二年(1095)前后的话,那么,原先苏轼心里那种“也无风雨也无晴”、“樽前不用翠眉颦”的洒脱、旷达,至此更多地让位于“多情却被无情恼”的伤感、哀怨,应该是符合逻辑的。
试把苏轼与辛弃疾(稼轩)做一比较,稼轩的英雄气概、入世之心绝不在东坡之下,论到词风豪放的一面,则稼轩更不输于东坡。然而,稼轩词作,既有表达建功立业的迫切感,也不乏壮志难酬的失落感;尽管终其一生孤傲倔强的精神挥之不去,但历经三次罢官的辛弃疾,愈到晚年,那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不吐不快的烦恼,就愈加在他的作品中显现。以辛氏五十岁后的两首作品为例:
一,破阵子·为陈同甫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有论者指出:该词前九句“可谓‘壮’之极也。但是,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却将前九句所述全部推翻。由‘壮’之极,变而成为‘悲’之极。”整首作品因此而成为“悲极之词”。(施义对:《辛弃疾词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其实,70年前在北京几所大学里教授文学的顾随先生(1897—1960。知名学者叶嘉莹、周汝昌都是顾先生弟子)在论及上引《破阵子》时说:“稼轩这老汉作此词时,其八识田中总有一段悲惨种子在那里作祟,亦复忒煞可怜人也。其实又岂只此一首?一部《稼轩长短句》,无论是看花饮酒,或临水登山,无论是慷慨悲歌,或委婉细腻,也总是笼罩于此悲哀的阴影之中。”(《顾随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八识,佛法唯识学中语,所谓“八识心王”是指是指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前五识是感识,认识具体对象;后三识具有抽象感念而非现实。八识田谓八识产生之处,犹言胸中、心田。)
稼轩如此,遑论东坡!
二,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抗金名将,被迫“闲居”,英雄无用武之地,为此感慨不已——春风吹拂,草木能由黄返绿,人的须发却不会由白变黑;青春不再,愁苦萦怀。我们怎能因作者自称“戏作”,及作品中诙谐的笔调,而对他落寞中的悲愤心情不予关怀呢?在赏析苏、辛这一类词作时,大可不必受“豪放派”框框的束缚,因作品中有豪言壮语,或闲适淡漠乃至幽默之辞,而无视作者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
“是真名士自风流”。真正旷达、洒脱、坚强的人,不会因其一时、一事、一篇作品中所表现的哀怨、悲观心情,甚至“八识田中总有一段悲惨种子”,而有损于他们豪放性格和英雄气概。
三,再创造的感受不能说成作者本意
汉代董仲舒有“诗无达诂”一说,晚清人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则称:“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与他同时代的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也有“虽作者未必无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有此意”的说法。
对此,有学者解读道:“……作者有寄托,通过作品来探索他的命意,但不要牵强附会;作者没有寄托的,要结合作品来探索作者的命意……读者可以通过作者所写的形象,结合自己的经历,提出作者所没有想到的感受,这是一种再创造。对这种再创造的感受,读者也可以发挥,不过不要说成是作者的本意,即解释还重在探讨作者的本意。”(周振甫、冀勤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
古典诗词确实可能为个性化阅读提供宽广的自由度,各人的理解可不一样,可读出自己的感悟。从这个角度说,由作品产生的感悟其外延几乎是无限的,但不能把自己的感受“说成是作者的本意”,对作者本意的探讨、诠释是有边界的。《蝶恋花·春景》的意境是“哀怨感伤,黯淡怅惘”,而由于作品中的形象“大于作者的命意”,所以读者可能在欣赏(不是解释、评析)时产生“再创造的感受”。以“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例,后人常常将这七个字作洒脱语,以至有人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已被国人用作安慰失恋者最经典的话,这是一种完全脱离原来文本“为我所用”的再创造,与作品本意完全无关。
常言道:“笑一笑,十年少”。但现在有科学家告诉我们:“悲观者”更健康长寿。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美国心理学工作者协会发表的一项对4万名成年人为期10年的研究显示,那些对“令人满意的未来”期望低的人实际上生活得更健康。相反,那些对未来“过于乐观”的人在10年内失能或死亡的危险性更高。该项研究主要成员、德国埃朗根—堡大学的弗里德·朗说,“对未来悲观可能鼓励人们更谨慎地生活,采取健康和安全预防措施。”
由此,我们是不是更加有理由说一句:给历史上和现实中旷达、洒脱、坚强的人物以及作为艺术形象的角色更多一点可以哀怨、悲观的余地吧!
(来源:新民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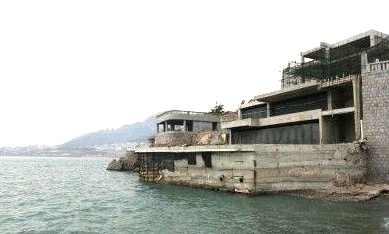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