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年11月8日,陈永龄参观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建院30周年成果展。

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永龄铜像在武汉大学落成,他的影响从广东走向全国。


陈永龄在1945年9月起至1956年11月于广州的中大、岭大及华工先后逗留了10年许,1952年10月-1956年11月期间任职华工4年。华南理工大学高教所陈国坚介绍:“平心而论,他在华工的时间不长,现今认识和了解他的华工人不多,仅有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1956之前的印象中。但这无碍于后人对他的评说。”陈国坚表示。在他看来,广州地区高校当年的重组,尤其华工的发展开拓相当艰难,而解放后的广州,作为大都市,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也已走过63个年头,“陈永龄正是当年参与广州市人民新政权创建的科技界、教育界的头面人物之一。”
组建工作基本结束后,陈永龄未及品尝华工的发展成果,便以华工副院长、武汉测量制图学院筹委会副主任之身,执国家之令,携原华工的测绘专业师生员工、图书设备,风尘仆仆赶赴武汉。
1956年,正是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前身)成立的那一年,国家把当时的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青岛工学院这5个学校的测绘专业合并到一起,并在武汉成立了武汉测量技术学院。著名大地测量专家、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宁津生195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测量系,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测绘学会测绘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的他毕业后分配到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工作,当时作为一个青年教师的他和当时兼任天文大地测量系系主任、副院长的陈永龄有了密切接触。就此,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现华南理工大学高教所陈国坚和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宁津生二位。
华工组建时期的开拓者之一
华工组建时期的开拓者之一
南方日报:华南工学院当时组建的时候有多困难,整个教学环境怎样?
陈国坚:“华南工学院”组建于1952年,当时定位为工业院校。广州市解放于1949年10月14日,它与外地同处国民经济恢复期与基本的社会主义改造期。作为蒋介石政权逃离大陆前的临时“京都”——后来的新解放区,它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以及肃反等较之外地晚了一步,任务也特别的重。那时,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师生员工,许多人包括部分中老年教师,对省市人民新政权及新秩序并不适应,以观望的心态注视着社会的变化,心存陌生,甚至惶惑。党和人民政府学习城市的建设与管理,建设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高等学校,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学,需要一批有思想认识的知识分子,率先站出来表达归附人民政府的心声,以利在爱国、爱新社会的大前提下,团结与调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尽相同的各方人士,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南方日报:陈永龄对华工的组建以及后来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的身份在当时有何独特之处?
陈国坚:陈永龄是当年所谓“先知先觉”的、即思想领先一步的广州地区知识分子先进群体中一分子,是敢于表露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勇气、投向人民阵营的心迹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
1950年暑假,陈永龄作为名教授参加广东省文教厅组织的广州地区专上学校首批思想改造学习。事后的10月初,藉着先前他在文教厅主办的机关刊物《广东教育与文化》上撰文《我们怎样了解自然科学的阶级性与党性》袒露思想之余勇,再撰文道:“以往我对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与党性是存在半信半疑的态度,我知道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超阶级立场和纯技术观点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尚无法说服纯粹自然科学者所提出的相反意见。这次学习上给了我有力的武器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在国外、在旧中国生活了40年的这位老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人生观的改变愿望或选择的背后,可能意味着当中曾有过的脱胎换骨般痛苦的思想斗争与心理的煎熬。既然他选择了新时代与社会,那么人民政府也就选择了他。1952年10月7日,原私立岭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的陈永龄,被广州区高校调整委员会任命为华南工学院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统领教育、教学管理之职。毫无疑问,他做了推行院系调整的“领头羊”。
南方日报:他在华工具体做了哪方面的工作?
陈国坚:以陈永龄的学术地位与声望,如果他执意抛开教育、教学管理,单独选择学术研究路一条,他完全有能力早出成果、多出成果的;但是这位大学问家毅然置个人之得于不顾,挑起教育、教学管理领导之责,将个人才智贡献于华工4年整。其间,他曾数度发表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表达师生对新社会、新生活的渴望。1954年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广州分会筹委会集会讨论新中国首部宪法草案时,他表示:“我们科学工作者本身也已改变了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用实际行动来迎接第一部人民宪法的公布;必须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同年9月底,他以高等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为题,畅言华工关于学习周总理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体会,于广州市首届人代会上作大会发言。表达师生“我们怎么能够不欢欣鼓舞,怎么能够不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呢”之心。此外,他在广东、广州科学工作者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座谈会上,慨言推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社会责任,还不断奔忙广州与武汉间,尤其是他曾经投书南方日报,就学习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结合全国天文大地测量高等教育现状、应用前景,畅论向科学进军的认识以及个人进军计划。
南方日报:但似乎在匆匆4年之后他便奔赴了武汉,这期间是什么原因?
陈国坚:1955年4月后,学校组建工作基本结束、国务院陆续任命华工正副院长,似稍可歇息之际,陈永龄未及品尝华工阶段成果,便以华工副院长衔武汉测量制图学院筹委会副主任之身,执国家之令,携原华工的测绘专业师生员工、图书设备,风尘仆仆地赶赴武汉,与青岛工学院、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有关专业的师生,一起筹建测量制图学院。后来陈永龄正式地调离华工,全身心地投入他终生的事业:天文大地测量。以后,他在国家测绘总局担任总工程师,继而运用全国之力组织队伍,于1975年完成珠峰高程的科学测量。
所以,他最应该被人记住的是:敢于担当。即使他在华工只有4年,但在1956年华工上下乐见其被评定为华工3名一级教授之一,他在华工的影响可见一斑。
靠听学习新技术,
和夫人感情好
写文章和讲课都是一流
据陈俊勇回忆,陈永龄的文采非常好,写文章和讲话是一流的,“陈先生讲课非常好,他嗓门很大,字又写得好,英文写得很流利。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基本只需要简单地看书复习一下,就完全懂了。他书也写得好,非常精炼。虽然后来大学的大地测量教材不用他的《大地测量学》了,但还是有很多用他的当作底稿,他的文学水平一流,表达极强,逻辑性也强。”
■趣闻轶事
靠听学习新技术,
和夫人感情好
陈永龄和夫人两个人外文都很好,所以高棣华会念一些国外的文章给他听,因为眼睛不好,也不能做笔记,只能靠听来学习了解新技术。“他写文章都是口述出来的,让高老师或者儿子写下来。他本来眼睛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打篮球把眼睛打坏了,那只眼睛不能说完全看不见,但是视力受到很大影响,之后只能用另一只眼睛看东西。由于长期使用一只眼睛,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两只眼睛几乎都看不见了。我记得我出国时候的推荐信需要他签字,他把纸放到眼睛边,或者用一个放大镜看,非常困难。”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大地测量专业、新中国成立后测绘界第一位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测绘局科技委员会主任陈俊勇回忆说。“他们夫妇俩感情很好。在武测的时候,有一次,两人骑着自行车在学校的林荫道上相互追,那时候他们大概五六十岁了,站在路边的学生们看到笑死了。”
写文章和讲课都是一流
据陈俊勇回忆,陈永龄的文采非常好,写文章和讲话是一流的,“陈先生讲课非常好,他嗓门很大,字又写得好,英文写得很流利。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基本只需要简单地看书复习一下,就完全懂了。他书也写得好,非常精炼。虽然后来大学的大地测量教材不用他的《大地测量学》了,但还是有很多用他的当作底稿,他的文学水平一流,表达极强,逻辑性也强。”
“文革”时被请去做顾问
陈永龄作为科学人的学术态度非常严谨,为人从不张扬,而且很爱护和提携晚辈。“上市80年代年轻人留学回来之后,感觉不够受重视,他和一个地质部的老院士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国内的专家,探讨如何发挥地学界年轻人的作用,如何在地学界开拓新的局面等问题。”此外,“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测绘局被撤销,但因为他有能力,国家总参谋部测绘局还特意请他去做顾问。
完成中国当时最大的测绘工程
南方日报:1956年,高教部决定筹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陈永龄积极参与主持武测的筹建工作,并在建校后任武测副院长兼天文大地测量系系主任。当时,您进入武汉测量制图学院,能回忆一下你们共事的情景吗?陈永龄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上,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宁津生:他的学术水平很高,特别是在高校担任教师,学生首先看中的是教师的学术水平和他在教学中的能力与表现。可以说,他是我国在测绘科学方面,特别是大地测量学方面的泰斗,中国的大地测量这一套教育、科研以及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是陈先生奠定的。当时在武汉测量制图学院,陈先生讲课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他讲课的一大特点是讲述清晰、理论分析透彻,讲课非常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尽管我当时已经是教师了,但我经常去听陈先生的课,我觉得听陈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
陈先生对新生事物、新技术非常敏锐,接受起来非常快比如说卫星定位。我记得那个时候陈先生的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了,他为了吸收这些新技术,让他的夫人把专业文章念给他听,在听的过程中进行思考,甚至于可以写出对中国这个技术发展的方案,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新技术。
南方日报:陈永龄被称作是我国大地测量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应该怎么具体理解他的开拓和奠基作用?您如何评价陈永龄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
宁津生:在解放前,中国的大地测量工作没有一个国家标准来指导和约束大地测量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组织建立国家的大地测量标准,我们称作《大地测量法式》,它规定了在中国进行大地测量的规划、设计,以及大地测量工作中的具体的技术规定。这是在陈先生的领导下完成的,这个《大地测量法式》到现在还在使用,它是一个科学技术的基础。
大地测量的主要任务是点位控制,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很多控制点,要把它的平面坐标和高程精确地定出来,这是今后其他测量工作的起始点,因此就要在全国建立全国天文大地网。在解放初,我们自己还没有力量来建立天文大地网,而是从苏联普尔科沃天文台引到中国来的。我们用了10多年的时间,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了一个全国含有5万个点的天文大地网,叫做“1980西安坐标系”。当时在国际上,我们建成的这个控制网的精度、规模,比美国、英国还要大,这个网就是在陈永龄先生的亲自主持之下完成的,包括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完成了称得上是中国当时最大的一个测绘工程。
南方日报:在当时的情况下,陈永龄测量出珠峰高程具有怎样的意义?
宁津生:因为珠峰是世界的最高峰,世界各国都盯着这个高峰的数字,以前世界使用的珠峰高程的数字是英国人测出来的,而且很粗糙。珠峰既然在我国领土里,我们应该自己精确地测量它的高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决定在1975年测量珠峰高程。由于珠峰所在地区的环境非常恶劣,在珠峰搞测量工作相当的困难,有些地方人都没法进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进行测量工作?怎样把珠峰高程测出来且与国际接轨?这需要一套很好的方案。
当时整个高程测定的设计、施工、数据处理这一系列方案都是由陈永龄制定的,他利用已有的珠峰高程测定的方法,同时吸收国外先进的测绘技术。在当时,与国外相比,我们的测量是非常精确的,由登山运动员带一个毡标到珠峰顶上去,在测量珠峰高程时瞄准毡标来测,再量出毡标的高度,用总高程减去毡标高度;其他国家测量则是用仪器瞄准所谓的山头,山头在什么地方却不清楚。另外,珠峰顶上有积雪,以前所公布的数据都是按积雪顶测量的,因为积雪会消融也会积累,因此这样测得的高度是不定的,而我们要测量的是它的岩石面,也就是说是一个固定的数字。1975年测定珠峰高程的时候,女运动员潘多带上了一根细竹竿上去,直接测定积雪的厚度。陈永龄所设计的这一套测定珠峰高程的方案是非常科学的,所以当时我们测出珠峰高程8848.13米这个数字,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当时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
对青年教师培养呕心沥血
、
南方日报:陈永龄十分重视和关心对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培养,他是如何培养青年教师或学生的?您当时作为青年教师,有没有受到他这方面的教诲?
宁津生:当时,由于中国测绘技术不如当时的苏联,国家当时“一切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教学包括课程内容和设置等各个方面都学习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为了更好地办这个学校,学校当时从苏联聘请了几位我们在这方面比较缺少的专家到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来教学1年。我们从苏联的莫斯科测绘学院(今莫斯科测绘大学)聘请了一位研究地球重力场和地球形状的教授来学校讲课,因为我们的俄语水平普遍不高,我在同济大学念书的时候,曾经被选拔去苏联留学专门学习过一年俄语,就被学校指定为这位苏联专家做专业翻译。当时陈永龄先生是学院管科研、外事的副院长,可以说我们之间是比较亲密的师生关系。
我在做苏联专家的专业翻译的时候,陈先生为了使我能更好、准确地翻译出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对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尽管我在俄语专科学校专门学习过一年,但他认为这个基础还不够扎实。所以他又专门从武汉大学请了一位苏联物理专家的夫人到学校来,给我一个人讲俄语口语,讲了整整1年。苏联专家来之前,他为了测验一下我的翻译水平能不能达到他所期望的程度,陈老亲自在台下听我做的翻译,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确实是呕心沥血,这一点我是亲身体验到的。
南方日报:陈永龄十分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1957年他在题为“与青年教师谈进修问题”一文中指出:“只有教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才能使高等教育质量不断地提高,才能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迅速赶上国际水平。”当时他提出这样的命题是否也有一定的时代背景?
宁津生:陈永龄和其他的几位老先生比如夏坚白,王之卓等等,他们知道解放前中国的测绘科技和教育的状况,因为他们曾都是留英留德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测绘事业和测绘教育相当重视,这些老先生在解放前的学习和工作期间,都有一种爱国之心,感觉到要用科学救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感受到新的政府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内心感觉到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因此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也非常重视。
不仅陈先生如此,其他老先生也都是这样,他们教育我们首先要提高政治水平,要学会做人,其次才是业务水平。陈老常说,“做学问和做工作,如果只是为自己,那是做不好的。”
为测绘学科打下了坚实基础
南方日报:在武测任职期间,陈永龄制定了一系列的学年工作纲要和科研工作计划,为武测后来的发展奠定基础。您如何评价陈永龄在武测的工作和成果?
宁津生:当时,高教部为了成立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筹备组,陈永龄先生当时是筹备组的副主任,从学校的选址到后期的建设、开学,陈先生在这其中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亲自到武汉来选址,还包括基建、教职工的召集等工作都是陈先生所负担的工作。到了学院成立之后,他担任管科研和国际交流的副院长,又是天文大地测量系的系主任,一个新的学校,首先要把学科的基础打好,不管是学校的基本建设,还是教师队伍,天文大地测量这个学科专业的发展,都是陈先生在这里打下的坚实基础。他1959年被调到国家测绘总局当总工程师,就这3年的时间,他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南方日报:20世纪40年代,陈永龄致力于大地控制网的布设理论和中国地区地球开关(大地测量学水准面)方面的研究,后来又在领导闽赣铁路线的勘测工作时提出利用航空摄影的方法进行勘测,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对于中国铁路路线勘测有何意义?陈永龄当时的提法对大地测量产生了什么学界反响?
宁津生:航测不是他的主专业,当时的专业没有现在分得那么明晰,作为老一辈的测绘专家,除了关注自己的主要专业之外,还要注意其他的专业。以前,中国铁路勘测的方法是用大地测量的方法,他感觉到老办法太麻烦,而且在深山老林里做大地测量工作非常困难。这在当时来说是对铁路勘测的一种新技术的引进,大大方便了铁路勘测的工作,他的知识面比较宽,也比较聪明,所以想到了这一点。
建国初期,我国使用的大地测量坐标系统的标原点是前苏联玻波尔沃夫天文台,1978年在陕西省泾阳县,新中国建成自己的大地原点。这项工作开始于1975年,陈永龄参与指导工作,是队伍中的重要一员,建立天文大地网,首先就需要建立大地原点,建立原点的方案都是陈先生制定的。中国大地原点的建设工作,我参加了其中的计算工作,陈先生制定方案时非常严谨,广泛地征求大家的意见,找我们一起讨论,在执行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去现场检查。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周豫
实习生 刘扬
(来源:南方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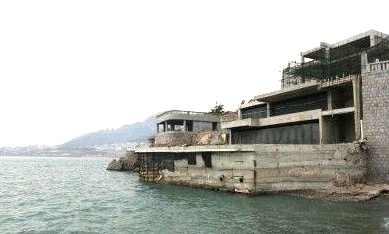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