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开生一把琵琶在手,演尽评弹韵味。

年轻时的赵开生在长城上练习三弦。

赵开生与饶一尘演出照。

赵开生演出照。
苏州评弹名家赵开生:
梨园赋
古往英豪梦,今来儿女情,寂凉长夜街巷,谁家曲绕梁?阶前镜里,小弄堂口,恩怨情仇多少事,粉墨唱平生。
遥想梅程盛景,大师光耀群星。九龙庭上,管乐迎兵来将往;虎度门外,青丝染暑炙寒霜。
至如今,欲净素手拈拙笔,写不尽——台前幕下、梨园惊世魂!
评弹: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是一门古老优美的说唱艺术。评话和弹词均以说唱细腻见长,以吴侬软语娓娓道来,演出中也常穿插一些笑料。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两人的双档,三人的三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三弦和琵琶。数百年来,评弹流传于江、浙、沪城乡,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2006年5月20日,苏州评弹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策划:赵洁
文:上海站记者 李媛
吴侬软语婉转间,弦琶琮铮拨心弦,若是少了评弹的抑扬顿挫、温文清丽,空有烟雨迷蒙的江南也就不再成为世人眼中充满魅力的江南。而在评弹界,说起名家,人们总要提到著名的弹词开篇《蝶恋花·答李淑一》的作曲者赵开生的名字,但赵开生却反复谦虚道:“我就是一个老艺人,老演员。”
开山弟子,别开生面
1936年初,赵开生出生于江苏常熟。小时候由于家贫,他只读了几年小学,14岁那年冬天,在同乡的介绍下,赵开生拜评弹名家周云瑞为师。进了师门,周云瑞把赵开生带到自己的老师沈俭安面前,说,老师给我的学生取个艺名吧。沈俭安定下了“开生”这个名字——一方面,他是开山大弟子,另一方面,希望他将来能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在当时,拜一个有名的评弹艺人为师,需要花不少“拜师费”,但赵开生家境困难,拿不出钱。“但老师对我很好,到上海后,老师还叫我多看电影、多看戏。我那时候年纪小,只以为是老师疼爱我让我去玩,后来才明白老师的一番苦心,他是要打开我艺术的门路,广泛吸收各种营养。”
初到上海的赵开生毕竟还是个十几岁孩子,淘气的他在生活上经常闯祸。比如:大晴天披着老师的玻璃雨衣跑出门,一脚踢在柜门上打碎了玻璃……周云瑞没有为这些生活琐事责备过赵开生,只是说:哎呀,你怎么老是闯祸?
“但我在学艺上,老师从来没有不满意过。”说到这一点,赵开生颇有些自豪。有一次,老师跟几个票友在家里弹唱,赵开生给他们伴奏,老师就说,这个小鬼,琵琶弹得还不错啊。不过,老师表扬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别人表扬我的时候,他就要批评我”。
15岁那年,赵开生在电台初试啼声,别人夸赞他唱得好、弹得好。师叔郭彬卿介绍一位女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说赵开生是“小小琵琶精,一对黄眼睛”。赵开生拿给老师看,老师生气了,打电话批评师叔。周云瑞就对赵开生说,“你可不要弄错啊,你的演出不是报纸上说的那么好。人家看你是青年,说的是新书,对你宽容。你现在是小孩子穿件大衣服,看起来很大,剥开来芯子只有一点点,不值得骄傲。”“现在我都懂了,老师是怕我被捧坏。”赵开生沉浸在往事中。
一曲蝶恋花,蜚声五十载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1961年春节,上海音乐厅,在大型交响乐团伴奏下,《蝶恋花·答李淑一》以评弹形式演绎,豪情激昂的旋律在音乐厅中回响盘旋,一曲终了,座下掌声如雷。人们都说,弹词开篇《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把苏州评弹推向全国、推向海内外的里程碑之作。而赵开生,就是这一“里程碑”作品的曲作者。1958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忙技术革新,评弹界也不例外,当时20出头的赵开生提出,用评弹谱唱《蝶恋花》,这的的确确是一项没有先例可循的大胆尝试。
“我觉得嫦娥、吴刚这些人物,都是我以前熟悉的”,赵开生告诉记者,这是他一开始选《蝶恋花》来唱的缘由,但他并不太了解整首词表达了什么,“所以我去翻资料,向别人求教,把人物关系弄清楚,把整体的情绪定下来:开头是比较深沉的悼念,但到后来,就是浪漫主义,英雄没有牺牲,他们是去月宫了。”
最大的难题是,现成的评弹唱腔都与《蝶恋花》配不上,那时候的赵开生也不懂简谱,怎么作曲呢?“我靠的是多年演唱的积累”。赵开生把原有的流派唱腔全部打碎,从第一句开始,用丽调(徐丽仙)的唱法,唱到“直上重霄九”,再改用沈调(沈俭安)的快节奏。吴刚用厚实的陈调(陈遇乾)点出其粗犷,而“寂寞嫦娥”就借来了歌曲《崖畔上菜花崖上红》里的曲调。“我感到,杨柳两位贵客来到月宫,嫦娥不再寂寞,她边歌边舞,啪的一甩袖子,这里就用了一个8度的大跳。”最后两句是全词的高潮,但评弹温文的风格不能提供足够的激情,于是,赵开生融入了京剧倒板的唱法。“后来我的老师周云瑞遇见我,说,你怎么会作曲的,我又没教过你,还是蛮好的!”说到这,已经年逾古稀的赵开生忍不住笑了,“我很珍惜老师对我的表扬”。
如今,这曲深沉炽热的《蝶恋花》已成评弹界一个历史印记,五十年来久唱不衰。
唱红《珍珠塔》 五斤竹笋当报酬
清代弹词作品《珍珠塔》是评弹的传统曲目,赵开生对它情有独钟。《珍珠塔》的故事并不复杂,相国之孙方卿因家道中落向姑母借贷,反受姑母奚落,表姐翠娥赠珍珠塔助他读书。方卿中状元后,扮道士羞讽姑母,与翠娥结亲。而评弹特有的细腻说表,将其中的人情世故展现得入木三分。多年来,赵开生非常喜欢这首曲子。
“我十几岁就跟饶一尘搭档出来唱《珍珠塔》。”赵开生和饶一尘同年出生,是同乡、同学,后来又都拜师学艺,是同行。15岁那年,赵开生和饶一尘先后回到常熟,两个人凑在一起练习《珍珠塔》。随后,几块板子搭了个台,俩人就去各个村子表演了。没想到观众爆满,他们连唱了20多天,每人拿了5斤竹笋当报酬。就是这“5斤竹笋”开启了两个人的同台之旅,在苏州,这对小双档开始小有名气。再后来,有上海的书场请赵开生和饶一尘。那时候两个人都才20岁上下,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也一炮打红。在这个书场的表演结束了,一大片“粉丝”的自行车、三轮车跟后面,转到另一个书场继续听。
一段时间后,赵开生决定整理完善《珍珠塔》。因为各派名家的《珍珠塔》剧本都有所不同,各有千秋,但从整体来看,剧本中却多多少少有不完整甚至矛盾的地方。“整理《珍珠塔》,我的压力很大,一是听众的习惯,二是一些老演员的要求,三是我本人小学也没有毕业,而《珍珠塔》那是才子写的。我改写的唱词,风格要跟原本相近,要是人家一听就觉得是硬装上去的,就不好。”赵开生先对人物进行了清理,每个出场人物都做一张履历表,一个人物出了几次场,做了些什么事,是什么样的性格,需要怎样起承转合,赵开生都列得一清二楚。
“我好像
从来没有玩过”
赵开生直到四十多岁才成家。“年轻的时候,我心里想着要把事业做好,觉得应该是先立业后成家。”
赵开生向记者感叹道,“我觉得,我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玩耍过。”退休以后,赵开生继续发挥余热,到苏州评弹学校担任客座教授。他告诉学生,唱快曲调时要注意有“肉”,唱慢曲调时要注意有“骨”。有时候,他还会去上海的评弹书场里当个观众,听一回书。
在赵开生看来,艺术不会一成不变,总是要从别种艺术门类中吸取新的养分。但与此同时,也不能丢开原来的魅力。“《蝶恋花》的曲子比较激昂,是因为开篇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可以喜怒哀乐。但总体来说,评弹不是一门靠激情取胜的艺术,它靠的是细腻。现在有些演员跟我说,说太慢了没人听,可我想,细和慢是两回事。比如说,吃西瓜就是要那种清香、清凉,听评弹,是因为它能给人的内心一块清静之地。”赵开生悠悠说道。
(来源:广州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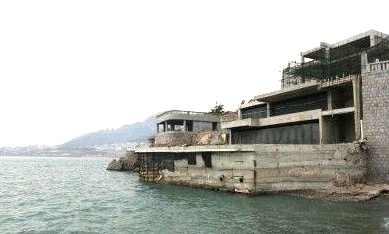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