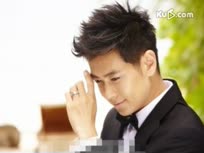樊建川:生于1957年,蜀地商人,抗战、“文革”物品收藏家,收藏有137件国家一级文物。现为四川省政协常委、建川博物馆馆长、汶川地震博物馆馆长。出版有《抗俘:中国抗日战俘写真》、《兵火》、《一个人的抗战》等。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爽 实习生 江雪文
在建川博物馆馆长、汶川地震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看来,民间博物馆出问题,相当于教科书出了问题。民间博物馆的生存乱象不能单方面苛责收藏者,行业净化需要政府负起把关的责任。
【编者按】
河北冀州的冀宝斋博物馆最近“火”了。
马伯庸在参观了这家博物馆后,写下《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一文,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这间由二铺村支部书记王宗泉创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间博物馆内收藏的大量“毁三观”的展品,包括有 “雍正年制”的金陵十二钗大缸、颠覆中国瓷器史的唐五彩人物纹筒瓶、“三英战赵云”盘,等等。
冀宝斋事件让公众看到了民间博物馆发展的一些乱象,也让公众对于民间博物馆的发展产生疑惑。据国家文物局官网资料显示,到2011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有535家,没有登记注册的大致还有1000家左右。535家民办馆,占了全国博物馆总量的14.91%。
然而,在民办博物馆蓬勃发展的背后,水平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现象却十分严重。收藏家马未都去年曾揭露过冀宝斋博物馆:“这件事现在反应这么强烈,我感觉挺奇怪的,这种博物馆到处都是,全国各地都有,很多的。”
台湾著名收藏家曹兴诚曾直言,各地民营博物馆越建越多,里面不少东西却是假的,“我去中国大陆南方,参观了几家民营博物馆,发现里面很多东西都不对,其中一家博物馆上下两层摆的全是假货。”
那么,中国现在的民间博物馆生存状态如何?民间博物馆里出赝品谁该负责?如何规范民间博物馆的管理?
一、 即便加强管理依然会有赝品出现
羊城晚报:冀宝斋博物馆被网友称为“雷人博物馆”、“赝品博物馆”,这是否是我国民间博物馆生存乱象的集中反映?
樊建川: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冀宝斋博物馆这件事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馆长知道是赝品还买,另一个可能是他不懂文物,就是着迷,着迷以后周围很多人给他参谋献策,说这个文物是不得了的,价值连城,他就买下了。我个人倾向于判断他是后者,不懂文物,而非有意让自己出洋相。我见过这种痴迷的民间收藏家,实际上买的都是赝品,被别人编故事骗了。
收藏爱好者自己要加强学习,多倾听方方面面真正懂行的人的参谋,用行话叫“长眼”,这是第一;第二是针对国家和社会管理层面、文物管理层面,文物单位可以请一些行家、专家帮民间博物馆进行鉴定和评估。
但即便管理,赝品问题是无法避免的,民间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世界顶级博物馆都有争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展品价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也有“开门见山”的赝品,一眼就可以看出形姿、题材、材料等存在明显问题。
羊城晚报:现在鉴宝的节目也特别多,民间对收藏的兴趣也特别大,但真正去学习欣赏和鉴别的人不多。这是不是一种浮躁的心态?
樊建川: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有一定的闲钱,这是所谓“盛世收藏”。人性形形色色,每个人的约束能力、知识专业水平和思维方式都各不相同。收藏家里就有一部分人特别认死理的,他只看他认为对的地方,一件东西有九个疑问但有一个对的地方,他就认为他是对的。每个人的脾气不一样,德行不一样,每个人对事情的判断不一样,思想方法论也不一样。
我主张发现一个细节有疑问就否定这个物品。 假设一件物品有十个方面作为评价标准,从材料、化工、颜料、印章等等可以评价这件东西对不对,如果九个方面看起来都是真的,但有一个方面有破绽,我就趋向于否定。例如一幅字画,纸是对的,用老纸仿造的,画工也特别像唐伯虎的,看不出破绽,但是印泥是新鲜印泥,或者内容上出现重大疏漏,那么我就可以否定这件东西,这样收藏起来就比较慎重。
二、民间博物馆的把关责任主要在于政府而非收藏家
羊城晚报:冀宝斋博物馆是一个村集体的博物馆,挂上很多政府的牌子,例如旅游、科普、爱国等,民间博物馆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收藏家马未都说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假博物馆,甚至带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与政府换资源。这种情况在民间博物馆中常见吗?
樊建川:我觉得他的动机没有这么下作和卑鄙,以我的判断,这些人是喜欢收藏,初步了解收藏,因为能力有限所以把假东西看成真的了。村领导想发展旅游,让乡亲们的饭馆、客栈、商店等有生意做,就必须有一个旗帜。大多数老百姓肯定也赞成咱们村有一个对外的品牌和吸引力,所以民间博物馆就这样做出来了。冀宝斋博物馆是全村人集体运作的资产,不是国有资产,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政绩工程。
跟政府换资源则是政府自己把关的问题。如果有人用博物馆换资源,我觉得这本身是个好事。问题在于政府方面应该请行家做一个评估,第一是研究藏品真伪,第二如果它是真的,应该被评估为乡级、县级、市级还是省级水平,评估后政府再决定给不给资源,给多少资源。收藏家都是痴迷者,有偏执的癖好,收藏家很少会从一开始就打算买一堆赝品来换政府的资源。所以把关的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而非收藏家,政府应评估这个博物馆资源值不值,放在我这里合不合适。
羊城晚报:问题是有的地方政府也不懂收藏,他见你做得有模有样,就顺便给你挂个牌。
樊建川:其实不仅民间博物馆要跟政府换资源,还有企业也跟政府换资源。如果政府官员不懂,你有文化部门等相应的职能部门,也可以借用学校和江湖上的行家进行鉴定。政府作为甲方,主动权在政府方面,用博物馆换资源出了问题也是政府的问题,收藏家的要求是很正当的。
羊城晚报:文物专家们不说真话或者愿意配合政府不说真话,这是不是收藏行业的普遍现象?
樊建川:那肯定了。现在有很多假专家,政府应该请真正的行家。所谓的行家,一类是在大博物馆见得多的,另一类是在社会上打滚的,特别是文物商人,他们反而是真正的行家,因为他们买每一件物品都牵扯到自己的利益,他们是真正好眼力的人。
三、保真度不高的博物馆应该被清理掉
羊城晚报:中藏网里的收藏爱好者对此事的反应尤其激烈,他们觉得官方文博系统想借此“封杀”民间博物馆,浇灭民间收藏者的热情。官方和民间两个收藏体系是否存在这种矛盾和冲突?
樊建川:坦白讲,官方博物馆里也有赝品,只是真品的保真度要高得多,民间博物馆肯定是良莠不齐。政府对展品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的民间博物馆进行“封杀”,我觉得是好事。有大量赝品的博物馆一定不能向公众宣传,它会导致整个民族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
博物馆是第二课堂,是公众受文化熏陶的场所,如果它的保真度特别低,会形成整个民族审美观、历史观、鉴赏能力的下降。这种误导就不仅是收藏家自己的事了。你在家里面摆赝品玩没问题,但当你的赝品要面对公众的时候,政府必须出手,把保真度不高的博物馆清理掉,这对国家、民族和收藏家本人是好事。任由赝品盛行,长远来看会致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受到损伤或者堕落。博物馆出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教科书出问题。
羊城晚报:现在民间博物馆的主题特别多样化,和官方博物馆相比,这些博物馆的存在价值和背后的驱动力在哪里?
樊建川:博物馆的价值在于民族文化财富的积累。财富是多种多样的,有春花秋月,有才子佳人,也有经验教训史,像我们做的抗战博物馆、地震博物馆等。总体而言,做博物馆的人都应该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认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有的人出于责任感做这件事,更多的人是出于爱好。我就是把兴趣放在第一位。
四、几十年后民间博物馆或占全国半壁江山?
羊城晚报:冀宝斋博物馆的情况一曝光,网民和媒体立刻疯狂嘲笑和质疑民间博物馆,认为这里面乱象极多,这种认知是否对民间博物馆发展不利?是否有行业自我净化机制?
樊建川:如果荒唐,嘲笑也是应该的。每个行当都有这样荒唐的事情,这没什么,众说纷纭是好事。
羊城晚报:你此前曾判断,未来的三十年如果政策鼓励和支持的话,民间博物馆有可能占到半壁江山。有统计数据称,是我国现在的民间博物馆经过注册的有五百多家,还有一千多家没有登记的“野鸡博物馆”。你怎么看待民间博物馆现在的处境?
樊建川:目前民间博物馆数量占全国总量的比率不会超过5%。我觉得不能光看博物馆数量,而应该看藏品的质量、数量以及展厅的面积。现在拍卖品大多被私人和企业买走,未来几十年,随着藏品更多到达私人手中,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如果国家政策能够给予引导和鼓励的话,民间博物馆发展到占全国的半壁江山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来源:羊城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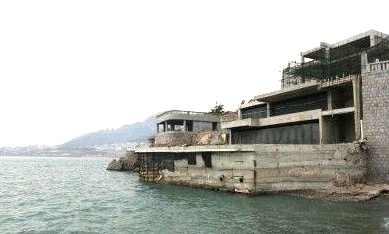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