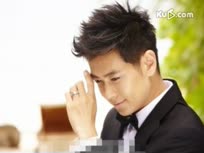今年上映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一片中有这样一个值得反思的情节:女大学生朱小北去学校的超市购物,被诬偷盗,撕扯中自己受伤,也打坏了超市的物品。学校管理人员采用了各打三百大板的方式——超市道歉,朱小北赔偿。感到备受侮辱的朱小北一怒之下打碎了超市的玻璃……朱小北的愤怒来自她寻求法理和人文的平等,而学校管理人员则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采取了传统社会中社群调整的方式,试图用“平衡”代替平等。于是,平等论者与平衡论者的决裂,导致了朱小北打碎超市玻璃的行为,并付出离校的代价。
这个小小的故事,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现象和问题的一个缩影,也可谓当前中国社会大型社会冲突和小型社会冲突的“寓言”:每个人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给予的东西,与这个体制所能给予的东西发生了巨大错位,而一些政府管理部门与资本拥有者很容易达成“利益共同体”的默契,给普通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当名义上的弱势个体无法在利益上获得真正补偿的时候,他(她)就不知道该如何维护尊严,从而容易出现一种踢猫式的迁怒攻击行为。
对于朱小北来说,她经历了两次“愤怒”:一次是感到自己受到一个超市老板的侮辱的愤怒,一次是感觉到这种侮辱不可能合理解决的愤怒。相对而言,第一次“愤怒”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最终消失;可怕的是第二次“愤怒”,在现有秩序和机制内不能解决。其特点是,如果老板骂了我,我没有办法对抗老板,那就去踢路边的猫。
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导致第二次愤怒,那么,这个社会的管理机制就出了大问题。而在中国,这个问题的典型特征是:一方面,总是通过各种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应法律法规的确立,承诺可以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不少普通公民却付不起诉讼成本、政治成本和生活成本。于是,“迁怒”就变成了愤怒的典型症候。
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踢猫”转移了愤怒,但同时也逐渐摧毁对社会主导体制的信赖,并相应促成对身边可见的人或者事的攻击习性。没有其他行为比攻击身边可以攻击的人或者事物更能缓解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积累性愤怒。这正是迁怒机制的作用:如果长期以来总是受到各种无法说清的抽象压抑的困扰,这种集体性的攻击行为,是具有强烈的狂欢效果和爆发性纾解功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同时完善社会主义追求公平合理的体制,将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必然面对的问题。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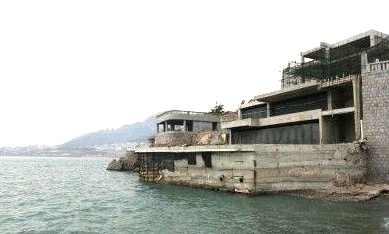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