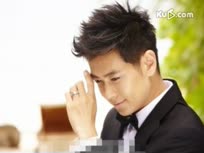大江参观鲁迅博物馆 摄影/李联朝

此图由gettyimages提供

大江(中)与莫言及《水死》译者许金龙的合影。
大江健三郎的《水死》中文版发布,向本报独家披露:该书差点胎死腹中,赴中国求助偶像鲁迅获精神力量
日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晚年最重要作品《水死》在中国发布。这是去年日本文坛两部“大书”之一,另一部是村上春树的《1Q84》。
大江表示,最初的写作想法来自他被日本右翼分子告上法庭的经历。而创作过程中莫言送的《楚辞》也给了他灵感,因为他的父亲和屈原一样都是死在水中。除此之外,这本书在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是什么样的题材让诺贝尔奖获得者写得精神抑郁?大江的中国作家朋友又给了他怎样的帮助?针对这些话题,本报独家采访了大江先生以及他的朋友、本书翻译者许金龙先生。
文/记者 吴波
唯一纪念
亡父的作品
《水死》的主人公以“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去世的大江父亲为原型,是大江唯一一部写给父亲的大作。故事讲述日本即将战败时,父亲响应青年军官建议,欲飞往“帝都”东京轰炸皇宫,炸死天皇以挽回战败投降的悲惨结局。但在一个洪水肆虐的夜晚,父亲携带“红色皮箱”独自乘坐舢板顺流而下,却因翻船溺水身亡,那只“红色皮箱”后被警察送回。
本书切实反映出二战前后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让我们得以发现潜隐在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负面精神遗产——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更让我们在绝望中看到希望——以“穴居人”为象征的民主主义之时代精神。
名家简介: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57年发表《奇妙的工作》,作为学生作家开始崭露头角。1958年的《饲养》获得第39届芥川奖,被视为日本新时期文学的旗手。1994年,凭借《个人的体验》、《万历元年的Football》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江的作品受到中国读者广泛喜爱。近期创作的《奇怪的二人组合》三部曲以及姐妹篇《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和《水死》等长篇小说,显现出作者在现实的绝望中左冲右突,试图为孩子们、为这个世界寻找希望之所的愿景。
《水死》的中文译者许金龙先生,作为日本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多年来专事大江健三郎及其文学作品之研究,曾发表论文《“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杀王”: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试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等,翻译作品《奇怪的二人组合》、《读书人》等,于2007年获得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
《水死》几次
陷创作绝境
为什么日本版和中文版《水死》封面都用红色?大江通过日本学者小森阳一、岛村辉回应表示,“父亲亡故后留下的皮箱是红色的,里边留下了很多创作的素材,包括书信等等,我多年来一直试图查阅皮箱资料,以便将这段事实构思为‘水死小说’,却因得不到母亲支持而无法查阅箱中资料。”
原来红色皮箱里边有很多对天皇“不敬”的资料,所以大江的母亲不允许他去查阅。等时间过去10年,大江终于得到红色皮箱的时候,却发现很多重要的资料在母亲在世时已经被烧完了。因为日本有一个习俗叫“晒虫”,每年夏天的时候会把箱子放到阳光下暴晒,每次晒完,母亲就会把一些敏感的资料烧毁。她害怕作为作家的儿子将这些写进书中而导致不好的后果。很多一手资料被烧毁,而与大江父亲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同辈老人也相继去世,这让大江的创作几乎陷入绝境。
创作过程中的另外一个打击,则是大江的儿子大江光。大江光是日本著名的作曲家,是音乐方面的天才,但却是先天智障,智商只相当于3~5岁的孩童。
大江与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是邻居。在创作本书过程中的某年圣诞节,小泽指挥了一个圣诞节音乐会,并将现场音乐录制成CD。回家路过大江家,小泽征尔将CD放给大江的儿子听,但大江光却直说“无聊”。小泽指挥的音乐被评论为无聊,让大江和小泽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年底,大江带儿子去东京大学附属医院体检时,才发现儿子的脊柱骨碎裂成三块,因为智商问题大江光不会发“痛”这个音,他的“痛”发音跟“无聊”一样!连儿子脊椎被摔碎父亲一点都不知道,这让大江深深自责,加上小说创作的瓶颈,这些令大江深感抑郁。《水死》的创作因此出现瓶颈。
赴中国求助鲁迅精神帮助
在抑郁的状态下,2008年,大江的一部作品获人民文学出版社评选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文学奖”,举办方邀请他来领奖。许金龙告诉记者,“获得邀请后,大江告诉我,他要来中国向他的中国偶像鲁迅先生寻求精神帮助,或许可以解决抑郁的问题。”许金龙说,当时大江住在国际饭店,他陪住。第二天凌晨6点左右,大江在房间里面对长安街,看着即将跳出来的“红太阳”突然说:“鲁迅先生,请您帮帮我!”
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是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最后一处住所。大江被众人簇拥着来到鲁迅塑像前时流下了眼泪,而到地下室参观鲁迅手稿时他又再次流下了眼泪。
大江为什么如此崇拜鲁迅呢?从大江与许金龙的一次对话中可知些许原因。大江说,“我从12岁开始阅读鲁迅作品,《孔乙己》中有一段文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这里所说的镇子,就是经常出现在鲁迅小说中的鲁镇。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就想,‘啊,我们村子里成立了新制中学,真是太好了!’否则,刚满十二岁的自己就去不了学校,而要去某一处的酒店当小伙计了。这一年是1947年,看的那本书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
读《水死》:
经典就是让人
永远读下去
“不好读”是多位专家在阅读大江健三郎作品时的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表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硬骨头,得慢慢啃,《水死》到现在都没啃完。作家阎连科坦言,自己专门留出三天的时间以为一定能看完,但才看到一半。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为什么这么难读?阎连科认为,一方面《水死》的结构叙述非常复杂;另一方面,大江健三郎的写作资源抽离了日常生活,进入完全书斋方式的、教科书的、图书馆式的写作,他几乎摆脱了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情感和世俗。
“对灵魂问题的关注,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对死亡的恐惧,对于核问题的关注等,都加大了阅读大江健三郎作品的难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文颖说。
作家、《人民文学》副主任徐则臣表示像大江健三郎这样的作家,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作家本人,就无法有效和充分地理解其作品,因为作家本人深刻地参与了小说的思想和意蕴的经营。徐则臣说自己之所以读完《水死》,是因为之前刚好读了《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得以把他的生活、创作和思想脉络与《水死》相印证。徐则臣认为,不仅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互文意识强,他本人的生活与作品也形成了互文乃至同构的关系。
作家崔曼莉坦言,《水死》到今天还没有看完,但非常高兴有一部没有看完的小说,因为这意味着生命中会有一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陪伴你。清华大学教授王成也表示认同,他说,所谓经典就是这样一个永远让我们读下去的作品。
对话许金龙:
大江储酒10年等莫言拿诺奖
广州日报:能给读者谈谈翻译大江先生《水死》的缘起吗?
许金龙:2010年12月2日,我与铁凝女士开会路过东京拜访了大江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目前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当时,我就确定要翻译这本书。
3月11日,也就是三个月之后,日本大地震。5月5日,我们又到东京开会,问大江那个小说创作得怎么样了。他说已经写了三分之二,但是面对日本大地震与核泄漏,无法再写下去。他说,按照以往的惯例会把它烧了,但是这次拿起来想烧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又放下来了。总之,这本书面世很不容易。
广州日报:当下,不管是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的翻译都没有很好的作品。大江文学在我国目前大致处于一个什么状况?
许金龙:坦率地说,如果不在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学术准备,恐怕是很难解读大江作品的。尤其是晚期的作品,大江更是有机地融入了此前很多作品的部分内容,从而形成了所谓“全体小说”。作为译者,如果不了解那些融合进来的原著内容和作者意图,是不可能完成这项艰难工作的。可我们最初在翻译大江作品时,由于出版社方面对时间的要求很紧,加之一些译者对大江的研究工作做得也不够,就使得很多读者抱怨“大江的作品读不懂”了。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用4年翻译大江所有小说。为了译好这套书,我们会把承担翻译任务的译者组成一个小组,大家定期或不定期地聚在一起,共同讨论翻译中遇见的难题。我希望,当这套书与大家见面的时候,“大江的作品读不懂”的批评会少一些。
广州日报:有传言,大江断定莫言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还特此准备了一瓶茅台庆祝,据说这瓶茅台放了10年之久?
许金龙:我记得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大江健三郎夫妇携长子大江光招待我们外文所一行三人,在外用过晚餐后踏上回程时,大江先生和我走在最后面,这时老先生突然问我:“如果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有何想法?”我回答道:“莫言是中国的优秀作家,我相信莫言先生终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江就告诉我,他在家里珍藏着一瓶尚未开封的茅台酒,要等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与莫言先生共饮这瓶美酒以示庆贺。此后十年间,我每年一两次拜访老先生时,他都照例会从楼上的书房里捧出这瓶茅台酒让我看;照例表示要等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与他共饮这瓶美酒,尽管医生早已禁止他饮用任何酒精类饮料。
(来源:广州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