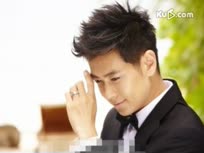湖北日报讯 图为:淤泥湖盛产团头鲂。
图为:渔舟唱晚。
图为:淤泥湖渔民丰收。
图为:淤泥湖岸古刹——报慈寺。
图为:公安三袁塑像。
图为:丰饶的淤泥湖。
淤泥湖位于公安县南部东经112°6’39"北纬29°48’0"
水域面积18.1平方公里
○水陆接触面积大国内罕见
○公安素有“百湖之县”“洪水走廊”之称
○团头鲂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很久以前,洞庭湖尾周边淤高,低处储水,淤泥湖因此得名。当地水利局的老人分析,淤泥湖可能是古洞庭湖的遗存。当地有句老话为证:“淤泥湖九十九个汊,抵不上洞庭湖一个坝”。
文脉深厚开宗派
厚厚的湖泥是农作物最好的肥料,深为老农所喜。淤泥湖的淤泥有多深?有个答案是10多米。
淤泥湖不仅物产丰饶,文脉更是深厚,在文化界影响深远。
公安县麻毫口镇文化站站长严汝坤说:相传,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爷爷过世,家人在打金井(俗称挖墓坑)时,挖出九十九只金龟。风水先生认为这是块大吉之地,劝袁家将金龟放生到淤泥湖的九十九个湖汊,这样就可以福泽九十九代子孙。
当袁家赶往淤泥湖放生时,天地间风云突变,山雨欲来,形势十分吓人。慌乱之中,袁氏族人将金龟全部放到淤泥湖的一个湖汊里。后来,“三袁”兄弟出生,一门三进士,创立文化上的“公安学派”。因为金龟只放进了一个湖汊,所以袁门只兴盛了一代。这个传说当然不是史实,世人却津津乐道。
一代文宗的诞生,与其说是沾了淤泥湖的脉气,不如说是汲取了明朝思想家李贽提供的“心灵鸡汤”。
当时,明朝统治者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原则,而这种“风化体”,则是“只看子孝共妻贤”。
针对这样的文艺思想与创作现实,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而“童心”就是“真心”,是人们“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贽提出文艺要表现“童心”,其矛头正是指向封建统治者要文艺成为孔孟之道的传声筒的理论。
在与李贽的长期交往中,三袁吸收了这种思想,提出了“性灵说”,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最终开创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公安派,开一代文学新风,当时“几倾天下”,其影响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陈独秀自称是公安派。
三袁之后,公安人才辈出。孟溪中学易先椿家,出了三个理科博士,被当地传为佳话。我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的开拓者王竹溪,当代著名作家陈应松等,都出生于这片热土。至今,淤泥湖畔文脉不绝。
聪慧机智誉中国
公安素有“洪水走廊”“百湖之县”的美誉。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是公安的魂,水是公安的命。
上善若水,智者乐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智慧的象征,蕴含着特殊的文化意象。空中俯视,淤泥湖宛如一尊大慈大悲的千手观音。千手观音,更是一种智慧的化身。
淤泥湖的智慧故事里,当然也离不开袁氏兄弟。故事里,“三袁”的外公“罗百万”是个狠毒的财主,对长工刻薄。袁宗道八岁、袁宏道七岁那年,栽秧时节,为了让长工开夜工,又不想出工钱,“罗百万”出了个鬼点子,让长工对对子。如对不出,长工们不仅没饭吃,还得开夜工。对子的上联是“稻草扎秧父抱子”,这可难住了没读过书的长工们。
傍晚时分,放学回来的袁宗道与袁宏道见长工们不回去吃饭,仍在做工。问清情况后,袁宗道告诉长工,以“竹篮提笋母偎儿”作答。袁宏道解释,稻草既是秧的父亲,竹篮也可说是笋的母亲。“罗百万”听了长工们的对语,非常吃惊,哑口无言,只好让长工们吃饭。
在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生活在淤泥湖畔的魏国贞,是民间智慧的代表人物。
从《魏国贞的故事》中可知,大约在1755年前后,魏国贞出生在淤泥湖边的刻木观。他祖辈几代都是种田人,11岁那年,他父亲与一财主打官司,不仅被占去田产,还被整死在衙门里。随后,母亲病故。他只得拿起讨米棍,身背破竹篓,过起了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饱受磨砺,魏国贞成长为一个爱憎分明、足智多谋、口才犀利、乐于帮助穷苦百姓、敢于抱打不平的人。
在“我是什么样子”的故事里,县官勾结杀人犯、纵火犯、惯盗犯,企图陷害魏国贞,人们不禁为魏国贞捏了把汗。待到魏国贞上堂,竟是那样滑稽可笑:将自己装在麻袋中,并声言:“自己有罪无脸见人。”在堂上,他对诬陷之辞毫不辩解。正当县官自以为阴谋得逞将要宣判时,魏国贞突然提出要三个罪犯当堂讲出他是什么样子。这三个罪犯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县老爷也慌了手脚。魏国贞出了麻袋,指着县官骂道:“你这狗官,竟敢串通囚犯,陷害良民,该当何罪?”县官从害人开始,以害己终结;魏国贞以被告开始,而实际以审判者的身份结束。
1820年,公安大水,地方政府不管,魏国贞造旨救灾战胜洪水,却被县令找借口用石灰呛死。魏国贞的行为最终受到朝廷肯定,他的机智故事更是广为流传。1984年,全国机智人物学术讨论会上,魏国贞的故事受到专家好评。
慈孝绵延两千载
纵观世界,孝亲、重家庭乃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在淤泥湖畔,这种慈孝之风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
淤泥湖距离公安县城的单边车程,有一个半小时。当汽车沿着狭窄的乡间小路来到湖畔报慈寺时,心里不觉为之一惊,穷乡僻壤间,竟有这么一座庄严宏大的寺庙。
走进报慈寺,各类建筑整齐划一,颇有气势。时近中午,天气正热,进入寺庙后,一颗燥热的心,顿时在一种安静祥和的气氛中平静下来。寺庙里只有一名老尼元玉和几个在此修行的居士,其他人早已外出云游。
说起报慈寺,60多岁的元玉一脸自豪:寺庙在国家有名,历史上是皇室家庙,现在规模在荆州排第一,最近申报了剃度权,马上就要批下来了。
寺庙中挂着二十四孝的故事,凸显出孝道文化在此的重要地位,继续演绎慈孝的传奇。
公元9年,王莽专权,刘秀母亲樊娴都为躲避杀身之祸,将刘秀安置好后,带领三个女儿避难淤泥湖,在湖东建庵隐居。后来刘秀起兵获胜,于公元25年6月在河北柏乡登基为帝,定都洛阳。刘秀来淤泥湖寻母回京,但其母未回,刘秀即命名其母居处为报母庵。此即报慈寺前身。事迹在《公安县志》有记载。
汉明帝继位后,佛法传入中国。汉明帝下诏,敕建报母庵,后改为报慈寺。唐宋明清以来,报慈寺屡毁屡兴,“为历代荆楚丛林之冠”。
湖东的报慈寺,说的是慈母在子孝亲的温情,而湖西的刻木寺,讲的则是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情。
二十四孝中,也有丁兰刻木的故事。汉末建安诗人曹植有诗,简短明白:“丁兰少失母,自伤早孤茕。刻木当严亲,朝夕至三柱。”
在淤泥湖畔,关于刻木孝亲的传说,版本不一,但均反映出大众对逝去亲人的追思,有能力养老时希望亲人还在。因而湖畔不仅有刻木寺,还有刻木观、刻木店等与之相关的建筑或地名。
历史钩沉
百湖痛失大半
淤泥湖渔场80岁的阳前福老先生说:解放前淤泥湖有3.8万亩,1958年围湖造田,淤泥湖水面缩小1万多亩,变成现在的良田。
公安县水利局局长陕学斌介绍,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公安有湖泊近300个,面积约300平方公里,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消失了近三分之一。1958年时,还有湖泊229个,面积261.8平方公里。经过大规模围湖造田,至1978年时,全县还有102个湖,共计104.7平方公里。“百湖之县,是过去非常骄傲的事。”
不过,2012年,经过湖泊“一湖一勘”现场调查,发现全县湖泊仅剩52个,面积89.27平方公里,其中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13个,10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3个。更让人痛心的是,原来掬手可饮的湖水,如今水质徘徊在四类左右。当年盛景欲说还休,早已不堪回首。
记者 张爱虎通讯员 熊昱实习生 刘志坚
本版摄影记者 张鸿 张爱虎本报视界网 谷少海宫安轩
(来源:湖北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