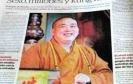南京籍70后作家葛亮,近几年一直活跃于香港文坛。昨天下午,他作为南国书香节中“南方国际文学周”邀请的嘉宾之一来到广州举行了自己首本描写香港的小说集《浣熊》的读者见面会,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葛亮表示,他身居香港,但心系南京。南京对他来说是“家城”,而香港则可比作“我城”。
谈到南京与香港这两座城市之间在写作上有什么区别。“前者是我写作的温床,后者给予了我写作的滋养。”可以说,小说集《浣熊》就是葛亮这些年观察、写作积累的结晶。
◎谈城市
以“过客”的方式写香港
南方日报:之前你的一些作品像《迷鸦》也有写过香港,新书《浣熊》是第一本完整的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但粤语使用得并不多?
葛亮:笔触有所不同,在《浣熊》中香港本土的意味更隆重、表达也更清晰。读者可以在书里看到一些粤语的表达,这对于营造整个小说氛围、对这个城市语境的把握有比较大的帮助。
南方日报:你已经在香港生活了10年,为什么选择这个节点写一本有关香港的书?
葛亮:我生长在南京,那是一个古典气韵非常厚重的城市,包括她的历史感都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香港的氛围很强调一种“集体回忆”的意识,在香港的经历会躬身反照到南京,南京是我称为“家城”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可以写、值得写,我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朱雀》实际上就是以南京为背景,从民国时期写到千禧年。
对于一个城市的把握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最好的,一种是你本来就处在这座城市的内核里,也就是“生于斯、长于斯”,就天然地拥有一种权利去述说;另一种是作为城市的“过客”,游走于这个城市,心无关爱没有负担、不需要为这座城市的细节负责。
◎谈写作
不停寻找自己话语方式
南方日报:《浣熊》之中,表达了你对香港怎样的发现?
葛亮:书中表达了我对香港这座城市的认知和很多传统性的细节,《浣熊》这本小说有很多意象性的东西,“岛屿”是其中一个,香港由周边大大小小263个离散的岛屿组成,这是一种离散与聚集的呼应。我们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可能都有一种明信片式的成见,但其实在这个后面还有很多传统性值得去挖掘。香港这座城市有关于历史的成分往往会被其更为繁盛的一面所遮蔽,但它最大的吸引力还是在于她的多元化,多元化带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她的包容。
《浣熊》这本书里面的小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相遇,在2008年有一个名为“浣熊”的台风,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包括世界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美国总统大选。在这样一个非常动荡的背景之下,自然界有这样一支非常有预兆性的台风出现,想表达的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一对非常普通的人的相遇,这种动荡是不平凡的。
南方日报:早前,台湾文学批评家李奭学把你的小说归类于“学院派”,《浣熊》算是一次突破吗?
葛亮:作为一个创作者,尤其是一个年轻作家,应该要不停地去寻找自己话语方式。当然,如果到了一定年纪,可能会沉淀下来,把其中一种方式作为自己写作的标志性风格,但目前来讲,我还是愿意去探索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浣熊》也是其中一种。
我对于细节的描写还是要得益于以前看的笔记体小说,寥寥数笔,跃然之上。小说里无论是对话或是场景,真正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寓事于虚。我一直有个习惯,做一些笔记写一些关于场景的描写和叙述,小说创作不一定是一个顺时序的作业,我有时候会突然在脑袋中蹦出一些特别有张力的文字描述或场景,就会立刻把它记下来,在小说其中一个章节加进去推进气氛,也会看电影寻找灵感。
南方日报记者 周豫
实习生 黄倩凝
(来源:南方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