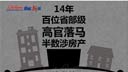1938年,与陈寅恪三个女儿的合影。立者是许燕吉与陈小彭,坐者是陈流求与陈美延。

1938年,许燕吉和父亲出游的合影。

1933年,父母结婚四周年纪念时拍的全家福。

背景图由Gettyimages提供

许燕吉家的小轿车。

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之女新书出版,讲述80年的曲折人生
近日,民国著名学者、作家许地山之女许燕吉的个人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出版发行,全书30万字,讲述了许燕吉从20世纪30年代到当下的80年人生历程,以个人的独特经历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一段动荡而飘摇的历史。新书上架之际,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图/记者 吴波
媲美《巨流河》的历史侧面
以个人及家族遭遇来侧面映照历史的书籍,近年来当属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最为有名,相比《巨流河》,《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更加贴近底层生活,用另一条曲线为我们展现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侧面:日军进攻香港时落在许燕吉家院子里的炮弹;昔日繁华无比的香港皇后大道残破楼底下那一片伸出手来求救的骷髅一般的人;前往贵州独山的火车道上那些坐在火车车顶被山洞挤下来或被烟呛死的惨不忍睹的死尸;在北京农业大学卢沟桥农场抬水、淘粪、抢饭吃、打狗、抓刺猬;在监狱里组织戏班子排练《雷雨》、《杨三姐告状》、《啼笑因缘》……
与《巨流河》悲壮的基调不同,许燕吉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一句情绪的波澜,没有一句话说自己很苦。也许经过80年人生历练,许燕吉终于能够以冷静、客观的心态来看待自己这些年来的曲折和磨难。毫无疑问,她这80年人生失去了很多东西,但始终没有失去的,是她的人生信念和对生活的坚持,她的这一辈子,恰如《落花生》一文中所传达的人生理念:“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作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
名门闺秀嫁给文盲老汉
许燕吉生于1933年1月,其父许地山是民国著名学者、作家,人教版五年级上册课文《落花生》即是许地山所作,这篇课文不知影响了多少中国人。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积劳成疾,去世时年仅49岁。噩耗传出,宋庆龄、梅兰芳、郁达夫等许多知名人士送了花圈、挽联。父亲猝死不久,日本人占领香港,母亲带着许燕吉和她哥哥逃往内地,辗转漂泊,流落于湖南、贵州等地。1950年,许燕吉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随后在“反右”斗争中,单纯而心直口快的许燕吉被定为“右派反革命”,入狱六年。这中间许燕吉经历了女儿夭折、丈夫为求自保断然与她离婚等人生惨事。
1964年,许燕吉刑满出狱,但因为仍顶着“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只能继续在监狱劳改队工作。1969年,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全国都在疏散人口以备战。许燕吉被疏散到河北新乐县大流乡坚固村。这是一个极贫困的地方,许燕吉辛劳一年所得还不如一头猪的工分多。自忖无法一个人在当地生存的许燕吉,只好去找在陕西的哥哥,并就此嫁给了当地一位目不识丁的50岁老农魏振德。
婚后,老实巴交的魏振德用行动感动了许燕吉。干农活时,他从不让许燕吉下手,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给许燕吉吃。有一次,许燕吉病了,魏振德整天整夜地守护在她的身边,即便白天农活再重,夜里都不合眼。望着五十多岁的丈夫心疼的神情和憨厚的举动,许燕吉感动得哭了,于内心深处接纳了这个乡下老汉,从此两人风雨相携。
许燕吉与陕西老农的这段奇特婚姻,几年前曾被数十家媒体争相报道,无数人为她在困苦环境中的遭遇而感慨,为她平反后不抛弃老农丈夫而感叹。而她的独特经历,更是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这段飘摇历史的典型缩影,映照出了中华民族在上世纪遭受的苦难和艰辛。
正如许燕吉在书中《前言》所说: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一段历史。对于许燕吉而言,历史并不仅仅是大人物和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无数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株花树,她希望我们不光要看到那些漂亮的花,更要看到泥土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
往事:
陈寅恪与梁漱溟曾住许地山家中
采访中,许燕吉还谈起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原来中国两个大儒——陈寅恪与梁漱溟都曾经长期居住在许燕吉家中。对于陈寅恪的印象,“他总是病殃殃的样子,他们夫妻俩身体都不好。我经常跟他的两个女儿一起玩,他们大人则在一边谈话,谈什么我们是闹不清的,我脑子里的陈寅恪是不苟言笑的,也不逗我们小孩玩。”许燕吉说,“现在也经常跟陈家人联系,他的三个女儿,老大在成都,是一个医生,老二在香港,学执法的,老三是学化学的。”
对于梁漱溟,许燕吉回忆,“挺没有架子的人。我爸爸妈妈晚上不在家的时候,他常给我和外婆及保姆讲故事。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了湘西赶尸的传说故事。他在我们家住到我父亲过世以后。他吃素我爸爸也吃素,所以他们能吃到一块儿去。新中国成立后,我去北京出差时就会去看看他。现在,梁漱溟的两个儿子,谁要是出书了也会给我寄。”
生活给予的苦难,没什么了不起
对话许燕吉:
生活给予的苦难,没什么了不起
广州日报:大家都读过《落花生》,但很多读者不知道许地山先生以及您一家人所经历过的这些人生故事,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一共花费了多长的时间?
许燕吉:我是学畜牧的,净跟牲口打交道,对文艺创作是一窍不通。怎么会想起要动笔写呢?因为最近几年,媒体觉得我有卖点,于是就邀请我去做节目。可是做完节目后,那些记者也不动笔,有的写了一些,我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还是自己写吧,起码真实。而且我的朋友们说,你的这一生跟国家的命运结合得挺紧的,写写也挺有意义的。就这样,我开始写这本书,前后用了三年。
广州日报:能给读者谈谈您父亲去世的具体原因吗?
许燕吉:他忽然之间就去世了。记得那是一个夏天,他先是得了感冒,跑到庙里面写文章,回来以后洗了一个凉水澡,当时还没事,可是15分钟后,他就死了,我们当时谁也没在他跟前。现在想来可能是感冒引起的心肌炎,但那时候不知道有这种病。
广州日报:您跟老伴在命运的安排下走到了一起,我想了解一下您现在是怎么评价已经去世的老伴的?
许燕吉:那个老头可聪明了,他曾说他比我和我哥加起来还要强。我说你连电话都不会打怎么会比我强?不过他确实不是一个笨人,就是不识字而已,他的父亲不是农民,外祖父还是武功县仅有的两个秀才之一呢。落实政策后,他跟我去了南京,以后在农科院干临时工。
广州日报:您在哪些时候会想到父亲的落花生的精神?
许燕吉:这不是想到的,落花生精神早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脑子中了。生活给予我的苦难,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总得生活,不能死了。我绝对不会自杀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死,活着要想办法,就这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
(来源:广州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