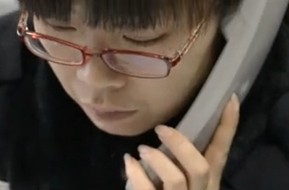美国记者渥塞
张晶晶
1956年12月22日下午六时,一架从莫斯科来的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舷梯上走下两名美国中年男子,他们是《展望》杂志驻苏记者埃德蒙·史蒂文斯和摄影记者菲力浦·哈林顿。三天后,35岁的美国黑人记者威廉·渥塞抵京,开始了为期41天的中国之旅。
就这样,上述三人成为冲破美国国务院禁令,首批赴新中国采访的美国记者。
1956年8月,中国首邀美国记者来华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做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尝试,1955年8月开启了后来持续17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当然,批准美国记者入境采访并不是一夜之间做出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根据已解密的外交档案,至少从1956年1月开始,外交部新闻司就有选择地对申请来华的美国记者本人和所属新闻机构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记者简历、影响力、最近言论、政治立场等。 7月间,外交部新闻司召集记者联谊会、公安部、中指委(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外交部美澳司等单位商讨接待美国记者的方案,并确定了组织和分工。
8月5日,我国政府正式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发电,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消息经美、英、法通讯社报道后,立即引起轰动:次日(8月6日)有10名记者来电申请访问我国;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是“违反护照法的”。7日晚,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提出只要在中国仍有在囚美犯,美国人赴华访问就不能被认为是 “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的”。美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其中尤以被批准记者所属报社的反对最为激烈,纷纷发表社论攻击美国国务院的这一决定。但美国国务院立即回应,再度表明其强硬立场。美国的报社老板们认识到美国国务院的态度已相当坚决,转而想各种办法钻美国法律的空子,争取来华。
20日,即美国记者可以入境的第一天,美国国务院代理国务卿小胡佛发表声明说:“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授权国务院表明,总统完全同意国务院在1956年8月7日就前往共产党中国问题所发表的政策声明。”在美国总统亲自干预之下,美国媒体陆续致电我外交部,表示不能来华,或延期至美国大选后再来。
为了继续争取美国记者来华,至9月4日我国又向一批记者发出了批准电;但他们都未能如期前来。而我方的准备工作仍没有松懈:新闻司的接待美国记者办公室暂不解散,继续准备材料;翻译人员仍集中在办公室继续学习;美澳司的同志暂回原岗位工作,但随时待命。
三名美国记者冲破禁令来华,被撤护照
1956年底,34名曾获准访华的美国记者中,有三名不顾美国国务院禁令,重新提出了访华的要求,他们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渥塞、史蒂文斯和哈林顿。
渥塞是美国两份黑人刊物的常任记者,一是在巴尔的摩出版的 《非洲族的美国人报》(美国最大的黑人报纸之一),一是在纽约出版的《危机》杂志,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无线电新闻部的代理记者。他很有才华,而且不吸烟不喝酒,对工作勤奋认真。他曾采访过朝鲜战争、亚非社会党会议、亚非会议,在万隆见过周恩来总理两次。他从反对白种人压迫有色人种的观点出发,反对美帝侵略亚非二洲的政策;支持尼赫鲁路线,主张“非暴力”等“和平主义”的立场。 12月15日,外交部新闻司批准渥塞来华做一个月的采访,24日渥塞在广州领得另纸签证入境。
记者史蒂文斯和哈林顿供职的 《展望》,是柯尔斯报系的一份图画双周刊,1948年美国大选时支持共和党内较开明一派。该刊在艾奥瓦州出版,每期行销200万份左右,特别畅销于美国中西部地区。史蒂文斯是该刊驻莫斯科的记者,时年46岁。据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了解,他长期在苏联,表现不坏,颇有才能,在美国新闻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通讯报道一般是比较客观的,较少主观猜测和造谣污蔑。哈林顿是摄影记者,时年36岁,为《展望》工作已经八年多,许多封面照片出自他手,未发现有什么歪曲污蔑的镜头。他们两人于1956年8月29日申请,9月4日获得我外交部批准,我驻苏联、瑞典使馆发给他们一次入境另纸签证。
所谓 “另纸签证”,根据我外交部1955年10月《驻外使领馆办理外国人入境过境签证暂行办法》第四章第十二条的规定,发给同我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人员签证时,都不在其护照上签证,而是单独签注在一张专用纸上。这种做法主要是说明我国还不承认这些护照。
入境后,史蒂文斯和哈林顿并不想声张行踪,试图避开其他在京外国记者和使节;但路透社记者漆德卫仍于12月26日报道了他们来华的消息。渥塞则毫不隐蔽,他来京后即与英代办处和印度使馆来往密切,24日外电已有报道。
对此,美国国务院的反应是逐步加强的:12月24日仅表示“遗憾”,到28日则发表公报撤销三人护照,并威胁要根据“资敌治罪法”冻结三人在美存款。
渥塞在29日晚上听到美国国务院已经宣布撤销他的护照以后,表示自己一点也不着急,待回国后慢慢打官司争取护照。他还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这样做很愚蠢,对美国政府不利,美国新闻界会同情来华记者的。史蒂文斯和哈林顿接到杂志社老板的命令要他们立即离华,他们的情绪因此受到影响;但还是顶住了压力,尽量拖延回去的时间,继续采访。
美国记者对什么感兴趣
史蒂文斯、哈林顿和渥塞抵京后,到外交部办理了外国记者登记手续,分别自1956年12月27日和30日开始在京采访活动。在华期间史蒂文斯、哈林顿二人曾前往上海、苏州、无锡采访九天,渥塞去上海十天,其余都在北京。
在京期间,三名记者在国际旅行社翻译的陪同下,游览了故宫、颐和园、长城、景山、中山公园等名胜古迹;参观了天主教北堂、基督教公理会、石景山钢铁厂、国棉一厂、荣宝斋、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第三玉器生产合作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儿童医院、中医针灸门诊部、妇幼保健实验院、第五幼儿园、中级法院(旁听审理离婚案)等单位;访问了画家齐白石、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政协委员翁文灏、《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和几位在华的美国教授和留学生等人;观看了电影、京剧和舞蹈演出。
他们在参观采访中,比较关注的问题有:解放台湾问题,美犯情况,我国留学生回国后情况以及对美国的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工资待遇如何,有否休假规定,各部门党、团员比例,以及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
红色中国的许多事物都让他们倍感新鲜。外交部新闻司的报告记录了史蒂文斯、哈林顿二人一些有意思的表现:
1.他们对古画、古物非常感兴趣,进了古玩铺就不想出来,并一再追问能不能出口。他们在24日和26日两天就买了古玩古画共值200多元,他们还一再抱怨80年以上的文物不能出境的规定。
2.他们在参观采访中提问题不多,也比较一般,主要活动是照相。他们拍的照片一般还可以;但对落后的镜头也很感兴趣。如一次在路上史蒂文斯看见小脚女人很奇怪,急忙叫哈林顿去拍,哈林顿表面上故意不拍;但实际上早已把小脚女人拍进了镜头。在儿童医院他们还拍了不少门诊部忙乱的情况和又病又瘦的小孩子。他们对中医很感兴趣,听说中药可以治绦虫,哈林顿表示他的朋友的儿子体内有绦虫,一直治不好,向院方索取了一包药。
3.他们在国际书店和东安市场看到斯大林的画像和斯大林的著作感到很惊奇,并说苏联在十月革命节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
4.他们在英国代办处门口看到有很多抗议英法侵略埃及的漫画和标语很感兴趣。
经过参观访问,史蒂文斯、哈林顿对我国的初步印象是:商品比东欧多,人民愉快,有效率,并很“习惯于”组织起来。史蒂文斯对于我国知识分子有无“独立思考”的自由有所怀疑,对于我们的思想一致甚感担忧,对我们的人口增长率也有所疑虑。
1957年1月18日晚,作家谢冰心、萧乾、郭小川、冯亦代请哈林顿和史蒂文斯晚餐,席间主要谈家常,气氛比较融洽。作协送给他们最近一期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哈林顿表示《中国文学》宣传性太重,全部都是农业合作化的文章,他表示希望看一些别的东西。他一再说,如果中国作家要把他们写进文章里去,不要把他们写成受压迫的工人。他说,他们工作很愉快,生活得很好,还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
三名记者在京采访活动的高潮是得到周总理的接见。 1月3日下午在机场,总理和史蒂文斯及渥塞握手时,哈林顿在旁照了相。得知和总理握手已摄入镜头时,他们很高兴。 1月6日傍晚,总理在龚澎的陪同下,分别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在上海探视美国犯人
史蒂文斯、哈林顿和渥塞分别于1957年1月7日下午和1月15日夜间到达上海。他们在上海的最大收获是获准探视了美国犯人。
史蒂文斯、哈林顿二人于15日下午3时到达上海市监狱,经办理登记和宣布接见规则后,3时25分与美国案犯分别谈话,3时55分结束。史蒂文斯会见梅保罗,哈林顿会见格类斯,主要了解犯人在狱中的饮食起居、健康情况和家属及外界的联系情况,是否“洗过脑”(如是否每天上课,能否看到些书报杂志,是否知道国际上发生的事件,能否祈祷)等,也问到其他犯人情况。梅保罗和格类斯按实际情况各自做了答复。史蒂文斯对美犯的健康、狱中生活(吃得好,能听音乐、旅行)表示惊奇,并说:“美犯在押期间的旅行比美国记者在中国旅行的地方还多。 ”哈林顿评论说:“从格类斯能吸乐根牌美国纸烟看出,美犯能接到国外包裹。 ”
整个会见过程都严格按照事先的规定进行。但史蒂文斯、哈林顿对不能照相一点很引以为憾,曾再三要求,甚至要求由我工作人员代照,最后史蒂文斯站在监狱门口由哈林顿照了一张相,作为采访美国犯人的证明。史蒂文斯、哈林顿当晚发往巴黎电讯一则,上海市公安局的报告称该电讯“内容一般,尚可,但不完全符合实情”。
渥塞搭乘的航班由于天气原因延迟,到上海时已过了规定会见日期。我方破例准许他于16日下午会见美犯梅保罗。渥塞十分感激,写信向外事处致谢。渥塞所问问题与史蒂文斯相仿,只是更详尽些。他还送给梅保罗从上海国际书店买得的三本英文古典小说。最后问了梅保罗对中国宗教问题和对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看法,问他是否有了“转变”。公安局的记录中说“梅保罗的回答仍然很好”。
会见当晚渥塞就向国外作了广播,并九次向国外发出电讯,报道内容大致符合实际情况,口吻比史蒂文斯的报道和缓,并推断说,中国政府批准会见是提前释放美犯的象征,并想借此来影响美国舆论。
史蒂文斯、哈林顿在上海期间,除会见美国犯人外,第二个要求就是采访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农民生活情况。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安排他们去虹星农业生产合作社采访。他们花了近一天的时间,深入了解了该社的总收入、社员的平均收入、农业税和收入的比例,地主富农参加合作社的情况,产品能不能由农民自由出卖、卖给谁、有无机械耕作,社内党组织及社主任(党员)本人入党经过等问题。但访问之后,他们认为这个社离城市太近,而且是“官方”介绍的,想另外找寻“真正的农村”,因此要求坐汽车去苏州、无锡。路上他们四次停车,随机访问沿途农村,采访正在修路或挖河的农民,询问农民对合作社的看法等。
渥塞除采访美犯外,还参观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市劳动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少年宫、儿童用品商店、徐汇天主堂、慕尔堂、国际书店、越剧院、上海制药三厂,访问了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并在某些公共场所和街道上录音。
作为第一批访问新中国的美国记者,他们的采访所得在美国将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因此除了会见美犯之外,他们采访的方针似乎是有闻必录。比较说来,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关注最多的民主自由问题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些都是他们注意的中心。
(摘编自学林出版社出版、朱纪华主编的《档案揭密外交风云》)
(来源:解放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