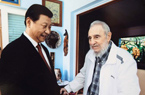记者见到梅墨生,适逢其“从容中道——梅墨生画书诗系列巡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始不久,回到北京的梅墨生在国家画院的工作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位戴着黑色眼镜的画家、学者,被认为是中国画、书法和近现代艺术研究与评论的“三栖型”人物,多年来他一直以率性独立的形象示人,坚守着自己的心灵高地。
遍求名师的“小杂家”
梅墨生的“不走寻常道”,在他小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他生来就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打小人们就叫他“小杂家”。“从记事起,我就喜欢写写画画,见到毛笔、印章、文字、书就喜欢异常,这是天性。”他说,上学之前,他经常用粉笔画画,帮大人画黑板报花边,“家乡有一个刻字店,有些老字帖,印章不是艺术章,是实用章,有象牙的、木头的、胶皮的,完全是工艺性的,那时我就跟着学刻字。”但梅墨生的兴趣远不及此,他喜欢下象棋,研究棋谱,还喜欢读书。他经常骑着自行车拜访不认识的人家,询问有没有老书和画册。他的书法启蒙老师是一个解放前的老国文教师,除了教他临帖书法,还指点他看古诗词、《古文观止》,这些都无形中激发着他的想象力,影响着他的艺术气质。
1978年,进入河北轻校就读美术专业的梅墨生,开始系统学习写意花鸟画,并且翻阅了从文史哲到80年代西方的美术艺术哲学等各种艺术相关的书籍,大量摘抄图书馆的古代画论书论,他还利用业余的时间拜访求教唐山当地的文化名人。毕业后,他辗转来到秦皇岛,干过许多装潢设计类的工作,后来还做过报社编辑,但骨子里还是喜欢纯艺术,他时常和北京的书画名家通过书信交流,得到了他们的欣赏和鼓励。1985年,命运垂青了这个始终怀揣绘画梦的艺术青年,这一年,梅墨生认识了太极拳大师李经梧和国画大师李可染,并拜他俩为师,从他们身上,梅墨生开始了自己艺术生涯的蜕变。回首过往,梅墨生感慨颇多:“这是我人生重要的时期,之所以对北戴河有特殊的感情,除了喜欢那里宁静的海,还有这师生的缘分。”80年代末,在李可染先生的勉励下,梅墨生在经历了一番周折后,进入了秦皇岛画院开始从事专业艺术工作。90年代初梅墨生来到北京,进入了中国画研究院即现在的国家画院,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职业画家、学者。
率性为艺的真性情
一个从容随性的人,他的艺术自然也是如此。梅墨生不做政治化的艺术,不做工艺化和商业化的艺术,而只为自己心性的自然流露,这是他的本性。他的作品古雅幽远,格调宁静,山水气象有离尘清远之风,花鸟作品则充满生命情味,又“以书法入画法”,雅趣天真,于道家的“平淡无为”中缓缓流露着一颗真性情。他笔法熟稔,线条富于变化,往往寥寥数笔,情韵毕现。这源自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精髓的把握,更得益于他对整个传统文化精神的领会。
梅墨生认为,艺术家动动手,从事一点审美表达,这是第二位的,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才是第一位的。他说:“40岁以后我就把艺术放在第二位,把文化修为放在第一位,更多做一个文化学者要做的事情,在传统的哲学,儒释道方面做研究。我对我的学生说艺术最永恒,文化最受用,身体最重要,其他都扯淡。我注重我当下是不是活得充实,第二将来能不能在艺术史上留下一笔。谁行谁不行不在这一时,而在历史。”
梅墨生在艺术界也总是以率真直言的形象示人。他的评论文章在90年代就曾声名鹊起,但2000年以后几乎拒绝写现代人的评论文章,很多研讨会也不参加,为的只是——说真话。“陈寅恪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向往这个境界,所以我不入任何圈子,不入任何帮派,我本来也无帮无派。”梅墨生坦言,虽然这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损失”,但自己并不后悔,“我关注艺术和学术本身,每天能有书读,有艺术可搞,我就很满足。”他说。
坚守传统的独行者
对于中国梦,梅墨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一个大国该有的情怀和文化自信,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他说,虽然我们的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破坏自己文化的现象一直存在,他举例说欧洲对历史文物的珍惜和保护意识极为强烈,但我们动辄就毁坏一个有形的文物或无形的遗产。除此之外,就绘画而言,“很多人拿西方的美学、西方的理念来引导我们自己艺术的发展,甚至于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这非常不可取。”而对于长期以来艺术界招生研究生的考试则表示不解:“为什么就凭一门外语就把考生的艺术才能拦截在门外?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正是因为有这样清醒的认知,才促使梅墨生把视角更多的精力投向传播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近些年梅墨生在武学、养生方面很有研究,未来,他还会把一些精力放在中西艺术美学的研究上,并最终形成著作。而这些,已经超出了一个艺术家的范畴。他一方面传播文化,一方面搞艺术,从理论到实践,从专业的教学到各种大学的讲座,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传播出去,“如果说对社会有所担当的话,那就是尽我所能,弘扬点中国的文化,给予我们的文化必要的位置和尊重,而不要去做那些以文化之名伤害文化,虚浮的、劳民伤财的事情。”
回思整个采访过程,梅墨生身上洋溢着游离于体制外的随性和从容,但你又能明显感受到他对我们艺术文化的强烈关注与热爱,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能更好的传承下去。从他身上,“出世”的艺术独立和“入世”的文化担当仿佛合二为一,不分彼此。毋庸置疑,在这样一个纷繁芜杂的世界里,我们需要这样的独立和这样的担当,因为,这是中国梦得以实现的真正动力。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