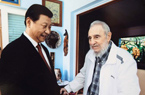草原,是他心灵的栖息地,也是他向世人呈现自己的窗口。走进他的草原绘画世界,你既会乐于徜徉在那种静谧的氛围里,也乐于聆听他画面背后的故事,和一颗心灵的悸动。他就是孙志钧,一个和草原有着不解之缘的画家。
那人那马那草原
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也是文革后第一届全国美展,一幅名为《月夜》的作品引起人们的关注:画面上,朦胧透亮的月色下,几匹浑身散发着银色光芒的马儿悠悠的伫立在蒙古包外,周遭是一望无垠的草原,宁静的画面,唯美的色彩,犹如一首安静的音乐,令人神驰向往。这幅有些“小资”情调的作品获得了展览的铜奖。人们也通过这样的作品,逐渐了解了一个来自蒙古的草原画家——孙志钧,而正是这幅作品,奠定了他的绘画风格。
《月夜》是当年在内蒙古下乡7年,作为一个知青的孙志钧一个片段记忆的沉淀。“那时夜晚的天非常低,非常静,星星低垂,银光满地,辽阔无边。”孙志钧描述道。人们会轻易的被这样的画面所捕捉并感染,而真实的情况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那些羊群趴在蒙古包周围,因为没有羊圈,要看羊防着狼,我们三个知青带着自己的马,轮流放羊下夜,条件其实挺艰苦的。”但为何画面中呈现的是这样的场景?“人的记忆是选择性的,艺术也是这样,它有生活,但当沉淀为艺术,就会自动褪去那些不美好的部分。”孙志钧说。
除了盖房子、秋天时打草搂草,放羊是下乡的孙志钧最主要的工作,“三个人一个蒙古包管一群羊,一千来只,每人配一匹马。”在孙志钧看来,马是和人关系最密切的动物,历史上人对马的依赖很大,它帮助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人类关系密切。许多艺术形象中的马是奔放的、激昂的,但孙志钧笔下的马却是安静的,不事喧哗,或悠然嚼食,或静伫远望,或漫步在夕阳下的归途。孙志钧说,这是草原上的马的真实常态,“一般人去草原看马都是浮光掠影的,但是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一天都看不到几个人,其实马的生活也是非常平静的,甚至是枯燥的。”但仔细看去,你又可以从他的画中感受到一种情节和静中有动的魅力。“蒙古包里透出光来,外面拴着几匹马,因为蒙古包里有人;夕阳下,骑马的人儿向着开阔的地平线行进,只留下背影,那是一天结束放羊后的归途。我喜欢画夕阳,那种回家的感觉,温暖的感觉,也是我的审美追求。就像人生,从这一段到另一段,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传统,是一条河
孙志钧对草原的眷恋,乃至于数十年对草原题材的钟爱,无疑和那段草原的生活密不可分。在那里,他结识了单纯的知青同伴,认识了淳朴的牧民,邂逅了钟爱的马儿,并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源泉和精神寄托。“我要画的是自己心中的草原,带有自己的空间、透视、色彩感觉的草原。”显然,草原在他那里早已不是一种简单的风景展示,而是一种记忆的沉淀,一种艺术的象征,和一个心灵的符号。
孙志钧的绘画为业界所称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自觉而主动的借鉴和吸收西画的元素,并融入自己的风格。在传统与创新这个命题上,孙志钧通过自己的绘画实践,做出了自己的思索和总结。在他看来,单一的固守某一种传统,或者一味循迹他人都是行不通的,唯有广泛涉猎并独立思考、探索,才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和语言。“传统像一条河,永远是流动的,不断丰富的。如果说水墨画是中国的传统,但唐宋以前工笔画是主流;宋代开始有了文人画,但那是很严谨的水墨,到了明末清初,石涛、八大、徐渭才开创了大写意,他们丰富了中国画的传统,而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创新的。所以用保守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画就把它僵化了,没有了生命。50年代的时候很多老国画家排斥黄胄,说他不是传统,但现在他成为我们的新传统的代表了。一个艺术家首先要尊重传统,但又不能囿于传统,因为他要表现属于他这个时代的东西,这就需要一些新的手法来搞创新,那创新从哪来呢?有可能是从传统中发掘新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从不同的艺术形式里汲取营养,而西方绘画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借鉴汲取他们的一些优秀的东西来表现我们自己就是一条很自然的路,而且这恰恰是对传统的一种尊重。”孙志钧走的正是这条中西结合的路子,事实也证明,他的这条路走的很成功。
文化兴梦美育化人
今年是甲午海战120周年,也是中国农历的马年,在这样一个节点,谈及中国梦,孙志钧说,中国梦既是民族的复兴梦,也是文化的复兴梦。一个大国的标志不仅仅是经济实力,还有文化的影响力,做好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创新是必经之路。作为一个画家和从事美术教育事业的人,能为这样的梦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很荣幸。在绘画上,从工笔草原到水墨草原,孙志钧一直没有停止对绘画的探索,如今他又在酝酿一种更现代、更概括但内容又很丰富的新画风,他说:“画家不能止步不前,在不同的阶段要画不同的画,很多老艺术家习惯于重复他们年轻时候的画风,因为体力等各种原因往往力不从心,如果不能适应这种转变,就很容易限制自己。有些东西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我们主动探索新的路子。”
作为北京工笔重彩画会的会长,孙志钧和多位同仁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当代工笔画的发展,在坚持严谨的学术水准的同时,帮助和发掘了一大批中青年工笔画家。而身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和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孙志钧多年的美术教育实践,见证了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他在为我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巨大进步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一些短板与不足。“美术教育对于人情商的培养、情感的滋养,乃至智商的开发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应试教育忽略了这些。一些专业的大学美术教育,是随着扩招起来的,掺杂了很多利益成分,但师资又没有跟上来,所以整体上并没有提升我们的艺术教育水准。而普及型的美术教育也有许多欠缺,在国外博物馆的教育是很大一块,但我国中小学对美术教育还不够重视,北京有这么多博物馆,但去看的人也不多,更何况更广大的二三线地区。但总体而言比过去连美术馆都没有好多了。”他说。
对话中的孙志钧,正如他的画风,宁静、简约而朴素,他的艺术生涯充满着一波三折,时代曾经无情的把他“抛”向草原,但同时又给他打开另一扇窗户,他在那里生根发芽,直至生长出自己的艺术延续至今,并把它融入自己的美术教育事业,这样的故事,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艺术的感悟,对人生、命运的思索,还有一份对责任的呼唤与内心的坚守。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