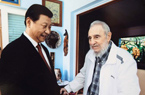著名音乐家 谭盾
董卿:今天文化讲坛的主题是“音乐、建筑与人生”,当然这个命题与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密不可分的,音乐家谭盾先生毫无疑问将会畅谈音乐,建筑家王澍先生毫无疑问要谈建筑,那么我,只能谈谈人生了。(全场笑)
“水乐堂”这个地方,它的名字本身就已经包含了音乐和建筑,“乐”——音乐,“堂”——建筑,它的名字我没有向谭盾先生请教过,是不是因为4年前《水乐》在这里首演,所以由这个作品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不过我相信今天两位智者的对话将会赋予它更多的内涵。
透过水这面镜子,既可以照出西方,也可以照出东方,还可以照出过去和未来
■当巴赫遇到禅宗,左耳朵听到的是东方的线条,右耳朵听到的是西方的几何。
■当我听到这里的水声的时候,突然觉得应该在这座破旧的粮仓中聚合一种氛围,让大家在这里听水,听东方,也听西方。
今天很感动。我记得我跟董卿有好久没见面了,跟王澍老师是一直想见就没见成,所以我特别感谢解放日报社能给我这个机会,给我这个缘分。
今天谈“音乐、建筑与人生”,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从水谈起,因为我觉得水是知道答案的。
水就是一面镜子,它好像跟我们的灵魂、生命和环境都有关系,通过水这面镜子,既可以照出西方,也可以照出东方,还可以照出你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当初,我来到朱家角这个特别有人文情怀的地方,感觉就是在这里听到了水的答案。
我们今天身处“水乐堂”,当初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呢?2010年我是上海世博会的文化大使,当时我们就考虑世博结束以后,怎么能让中国的世博之声留下来并一直传扬下去。要特别感谢当时青浦的人邀请我来这里采风,听这里的水,感受这里的水上人间。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很矮的粮仓。我在岸上采风,戴一副耳机,正在听巴赫的音乐。巴赫是 “古典音乐之父”,他的作品非常有哲理且又非常地数学化和几何化。忽然,炊烟升起来,对面寺院里的师傅们做晚课了,开始吟唱家喻户晓的 “南无阿弥陀佛”。我当时很感动,感觉左耳朵听到的是东方的线条,右耳朵听到的是西方的几何。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东西方文化到底是矛盾多,还是和谐多?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其实近代西方文化好像更多以科学为依据和发展脉络;而东方的文化更古老,永远是以大自然作为准则。
说起东方文化,我们最讲究的就是风土人情。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情、那么多的感情,对于我来说,超越所有感情和人情,与我关系最密切的就是音乐和建筑的那份情。孔子听《韶》乐,三日不知肉味,可见他认为音乐里面有人情,对于塑造一个人的精神来说就像建筑一样。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风土,讲究平衡,也讲究人情,造房子是,塑造人更是。从这点上看,音乐跟建筑的关系,真的太近了。
所以,当我来到朱家角,听到这里的水声的时候,突然觉得应该在这座破旧的粮仓与对岸的古老禅寺中聚合一种氛围,让大家在这里听水,听东方,也听西方,更能听到自己。
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如果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哲学通道,你就会发现没有矛盾
■第一次去纽约带了两件东西:一箱卫生纸和一本《楚辞》。
■东方文化的哲理跟天、地、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世界的未来就是天、地和人的未来。
东西方文化对我来说,永远是在和谐中去化解它们的冲突。
我第一次去纽约读书,那是1986年。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送我时,送了我两件东西。第一件就是一箱卫生纸,因为听说纽约买卫生纸很贵,(全场笑)那时候我们很穷;另外一件东西,就是我带了一本《楚辞》。《楚辞》让我回归,使我在纽约写出我的第一部歌剧《九歌》。卫生纸吗,到现在还没有用完。(全场大笑)
记得我刚到纽约留学的第一天,就碰上纽约第二大道有游行,我问他们为什么游行示威?他们告诉我,因为有一栋房子要被拆掉,那座房子是捷克闻名世界的音乐家德沃夏克在20世纪初住过的房子,他在那个房子里写出了世人皆知的《新世界交响乐》或叫《自新大陆》,结果开发商要把它拆掉。我看到当时跪在那里的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他们都说这个房子不能拆掉。他们说:“只要你建设,就会消亡。”
我当时觉得这个话说得很有意思,我们在拆建的时候往往没有想到有些东西却在加速消亡。其实那些音乐家说的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老城拆建”很相似,就像王澍老师的观点,建设要回归自然才好。
东方跟西方如果能找得到一个共同的哲学通道的话,你就会发现没有矛盾。为什么西方现在这么崇拜东方,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众多人口所带来的宽阔市场,更加重要的是,东方文化的哲理跟天、地、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世界的未来就是天、地和人的未来。
比方说,我从纽约回到老家湖南,我妈妈说我们要搬家了,终于要从平房搬到楼房里去了。她很严肃地对我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须你来拿主意。什么事呢?她说,到底是用传统的蹲式厕所还是用抽水马桶?(全场笑)我爸爸总结说,这其实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问题。(全场笑)
我跟我妈妈讲了西方抽水马桶科学上的好处:一是它通过水能把气味隔掉;第二是使废水和污垢的处理更加工业化;第三是清洁、卫生和环保。我妈是最难说服的一位传统的中国妇女;但也被我这几句话说动了。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跟她找到了一个共通的平台,就是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共通的平台:都是从环境考虑。然后我就发现,只要我们用心找到一个共通的平台,所有的矛盾都可以转化成和谐。
于是乎,我在艺术上永远在用心寻找那种东西方共通的哲学平台,无论两种文化多么遥远,有多么大的矛盾,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共通的哲学平台,就是胜利,就是创造,就会成功。
再举一个例子: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英国人说,一定要伦敦交响乐团来给交接仪式奏乐,因为这是一个英国人的和平之旅;中国人说,那不行,一定要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来演奏,因为这是中国的主权回归。为了化解这场争执,我就跟马友友先生讨论,我们能不能请200个香港小孩子代表未来,再用那套2400多年前的中国古老编钟,演奏出过去那种大自然的远古音律,通过马友友的大提琴作为桥梁,把过去跟未来连接起来,这才是东方和西方对明天香港的期盼。这个方案一出来,你就发现东方人也喜欢,西方人也喜欢。于是,我的《天·地·人》交响曲也就诞生了。
东方的韵律是以河流为琴弦、以天地振动作为音阶的,而西方是把听觉的音响化为阶梯
■东方的音乐基于自然,是流水,是点、线、面。
■中国人的园林是用人来感染的,是要用情来滋养的。如何激活这些世界各地的中国“睡美人”?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让风景有人气,接地气。
作为艺术家来说,我的最重要的理想,是找到东西文化的共通哲学平台,使我的艺术西方人接受,我的父老乡亲也很喜欢,我觉得自豪,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生存意义。
我发现,东方的音乐和西方的音乐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东方的音乐基于自然,是流水,是点、线、面,因为点和线的存在,才带来了面的无限可能。它的韵律就像东方建筑的韵律一样,是跟自然在一起的,是以河流为琴弦、以天地振动作为音阶的;而西方是把听觉的音响化为阶梯,它是通过量变,通过几何,通过数字通向精神王国。
所以西方可以把振动的听觉空间化为“do、re、mi、fa、sol、la、si”,再化为无调性。今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20周年——“双甲年”大庆,想起梅老夫子一韵,(哼唱京剧曲调),你说这个“do、re、mi、fa、sol、la、si”去了哪里?(全场笑)那是地韵、天籁,迷死西方人了。(下转第15版)
(上接第14版)
在我的音乐里面,永远有一个非常迷人的东西,那是我坚持的,也是我的父老乡亲和外国的音乐迷都可以接受的,那就是我把音阶体系跟中国大自然的韵律体系,结合成一个有机的体系,把音乐当成一个巨大的底座,不切割它,也使得梅兰芳先生的韵律一下子变得无限宽阔。音阶体系和有机体系把这两个东西融合一起,就变得非常有意思,成为了我。
“水乐堂”就是一个这样的实例。把朱家角圆津禅院的老调古韵,把那些感染了我们爷爷奶奶、先人们的千年文化保留下来,再把它和“欧洲古典音乐之父”巴赫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然后用谁来连接它们呢?就是水,水的节奏和韵律把它们连接起来了,成就了今天的“水乐堂”。
这种共通的平台,需要不断寻找、发现和发明。
作为一个指挥,我一直在全世界的音乐都市游走,无论是维也纳还是慕尼黑,或是伦敦、纽约,我发现,它们都有一处中国园林。可是,这些园林都像睡美人一样,成了一个个凝固的美女。
中国人特别讲究天地人的和谐,中国人的园林是用人来感染的,是用情来滋养的,是用景来传承的。现在该如何激活这些“睡美人”?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有人气,要接地气。
后来,我在研究昆曲时发现汤显祖的日志写得很有意思,他家之所以要有自己的戏班子,是因为每年的春、夏、秋、冬,他都要用不同的人情故事和昆曲乐韵去激活他的园林。这对我启发很大。
然后我又设法在东西方的园林建筑、音乐艺术方面找到一个共通的平台,我就想到我们可以做一个园林版《牡丹亭》,把昆曲和园林做成一体,把人和天地做成一体,这会让伦敦的人、纽约的人都为之感动。朱家角园林版《牡丹亭》做完以后,得到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的邀请。我们刚刚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园林里面演了《牡丹亭》,然后还将在圣彼得堡的冬宫、中国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展演,为什么?因为那里都有一处东方园林,看到园林版《牡丹亭》,他们突然觉得我们同饮一池水、同吸一口气,并有了一个共通的哲学平台,西方人觉得感动,东方人觉得自豪,我们就做起来了。
音乐和建筑实在是太像了,其中最像的一点,就是都要面对数学和几何,更要面对美丽的山水和大自然
■每一个民族的背后都有一条母亲河,每一个国家最崇尚的那条母亲河恰恰就是她文化的来源。
■历史是可以造就一切的,我们不能在造就一切时,忘记了自己是被谁造就的。
讲起东西方文化的共同点,我发现每一个民族的背后都有一条母亲河,每一个国家最崇尚的那条母亲河恰恰就是她文化的来源。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几条河都是我们的母亲河,从黄河一直到长江。上海的黄浦江运载了众多精英出去,也接回了无数精英回到故里。
我去指挥台北交响乐团,有一天,到晚上11点没什么事了,我就想去逛逛夜市,他们说逛夜市最好就是到诚品书店逛一逛。一到诚品书店,我发现满地的年轻人,都在看书,我也跟他们一样往地上一坐,随手取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 《女书》。书的内容很有意思,第一页就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南的一群山里的女人跑到北京说要去看望毛主席;但是她们的语言无人知晓,谁也听不懂她们的话。后来语言学家来了,发现这是女书,是千百年来由女人发明、只在女人中间流传的一种语言,而且它是通过母亲口传心授,教给女儿如何做母亲、如何做女儿、如何做妻子,它就是中国女人的“圣经”,是母亲河里面最宝贵的一滴水。
我一下子就钻进去了,花了5年时间做女书的研究。我在湖南江永发现了13位现存的女书传人,大部分都在90岁左右。5年以后,我发现只剩下了7位了。这个经历提醒我,历史是可以造就一切的,我们不能在造就了一切时,忘记了自己是被谁造就的。
我们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了《女书》,同时我们也要跟全世界最著名的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奏《女书》。通过这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母亲河,你可以看到最为伟大的中国女性是怎样造就的,你也可以看到,她后面的庄子在哪里,她后面的孔子在哪里,她后面的老子在哪里,全部都在那一条大河里。
《女书》的创作也让我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哲学平台和文化平台。当今世界,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女性文化系、女子文化学院都是很热门的。《女书》的问世点燃了妇女文化界从东方到西方的一把火,让大家去研判我们的母亲从哪里来,我们的母亲河从哪里来。
女书这么古老、这么与众不同的一种吟诵歌唱,之所以能够让全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让众多中外音乐人都感兴趣,我自己的体会还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东西方共通的文化平台化解了矛盾,化解了冲突,化解了误解,演化成了一种创新的力量。
一会儿王澍先生就要发表他对音乐和建筑的理解,我再最后说一句,我觉得音乐和建筑实在是太像了,其中最像的一点,就是都要面对数学和几何,更要面对美丽的山水和大自然。(全场鼓掌)
董卿:谭盾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音乐家。今天文化讲坛开始前,会场一直在播放谭盾先生的作品《卧虎藏龙》的主旋律,那么美,我们都能感受到作曲家深厚的古典音乐的基础。如果今天晚上大家在这里欣赏他的2014“水乐堂”开幕首演《天顶上的一滴水》,以后再听他的《纸乐》、《女书》,就能够感受到他的创造力简直是天马行空。
音乐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触动,大家都是深有感触的,有人说音乐会让你悲伤的时候更悲伤,快乐的时候更快乐。建筑同样可以触动我们的内心,舒曼在他的《第三交响曲》当中就想把科隆大教堂的雄伟表达进去,而对此柴可夫斯基的评价是,“你在我们大教堂的绝顶之美的感召下谱写出来的乐章,也将成为后人心中像教堂一样不朽的丰碑”,可见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据我所知,“水乐堂”不仅是观赏音乐的场所,它本身也是件乐器,因为时间关系,谭盾先生没有再向我们作更多的介绍,这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发出声响的?
谭盾:今天晚上观看演出大家就可以看到,比如说这里(指着棚顶)是一个水琴,它可以演绎和风细雨,也可以演绎莎士比亚的狂风暴雨。这是一个水地板(指着地上),它可以承载滴水穿石、踏水行歌的水摇滚。再看那个楼梯,那是我请湖北博物馆帮我把楼梯做成了编钟音梯,音乐家穿上木屐在上面走动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到“南无阿弥陀佛”(唱)的音调。
董卿:我现在穿高跟鞋上去行吗?(全场笑)
(来源:解放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