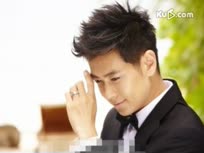“身份神秘”的歌手
老刘确有些真才实学。
他已有100多首诗词作品 “入编”,60幅大型书法作品“获奖”。他自认,书法作品一般,因为研习时间不长,2008年“才与社会见面”;但诗词方面,他颇为自得:“思想性、艺术性可以经得起检验,可进入一流水平。”
老刘在投稿之前,曾几经介绍,将几首代表作,如《粉碎四人帮》、《香港回归喜赋》,给广西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看过,对方赞许“还可以”;他也曾托人,将作品递交广西老年大学的老先生 “斧正”,对方赞 “这个人很有功底”,“有些不妥,有些很好”。
多首诗词“发表”之后,有组织授予老刘“文艺泰斗”,他不敢当;他认为,“当代艺术名家”这个头衔比较合适,受之无愧。
但不知为何,老刘拥有这么多 “荣誉”,却刻意低调。他所在的村子里,人们并不清楚老刘在民间文艺界的 “名望”;老刘那张“中国诗书画出版社”的社长名片,也只发给少数几个熟识的老友;村里因为征地问题,曾推选老刘到北京上访,但老刘到了北京,根本没动用自己在文艺界的“人脉”,也没有去拜访那些他担任要职的文艺社团。
问他为啥?他只是反复说,没什么好说的!不想跟人说!那些“挂虚名”的单位,没啥好去的!
老刘不会上网,没摸过电脑,但或许,他心里知道些什么。
也有朋友钦慕他,他的“事迹”上了当地报纸,有人前来祝贺;还有人,不时请他帮忙,写些应酬唱和的诗词,或请他修改。
他的朋友圈子,主要是当地“平话山歌”的歌友。每个星期天,他都骑电瓶车10多公里,去公园与歌友聚会。在这里,他的知名度的影响力似乎比 “民间文艺圈”更显著,上千歌友都认识他,喊他“三哥”,赞他为著名歌手。老刘在这方面确有造诣,倒是真正“传承传统文化”——他各个村子跑,收集了3000多首山歌的歌词,用毛笔抄录,复印后分发给歌友;他精研曲调,时常被众人拉着请教;他能临场改歌词,唱得幽默,对歌时引得旁人咯咯直笑。
不久前,歌友们组织了 “山歌大奖赛”,老刘去铁定能拿个“荣誉”,但他为了赶庙会,压根没去参赛。
他心底觉得,这比赛“一般上台就有奖”,没啥意思。
“成名”后的梦想
虽然不少人觉得,老刘最擅长山歌,但他志不在此。
他是聪明人,曾在南宁一中读书,1958年免试进入广西机械工业学校大专班学习;后因言获罪,回家务农。
无论在哪里,他总是会动些小脑筋的。他养猪卖猪,被人举报“不义之财”;他私下种了4厘地的果子,又遭批判。务农近20年后,因他在瓜果种植上颇有技术,被生产队推荐,成为南宁新城区青年园艺场的老师,之后进入南宁自行车厂,做过技术员、分厂办公室主任和工会主席。
但一直到他1999年退休,老刘所获得过的荣誉,是连续多年的工会“优秀工作者”,无它。
他总觉得,还能做些什么。于是他主动提出,编修族谱。他费尽心思,四处寻找刘氏家族的墓碑,抄录碑文,与地方志相互比对,然后用毛笔誊写,复印后送到每一户族人手上。
修了族谱后,村里决定要给祖宗墓立石碑,老刘撰写了碑文。然后,唯一一次,他在村里讲述了自己的“荣誉”,并提出,想把自己的名字和头衔刻在石碑落款处。他心里已定了最为得意的“头衔”——“世界民间文艺十大杰出终身成就艺术家”,据说是“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授予的。
老刘认为,这样做不仅能“让自己更有名”,还能提高家族的知名度和支持度。但村里人不同意,老刘觉得是“有人眼红”,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或许,老刘觉得,自己若再有名气些,村里人就不反对了。
他“自费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与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双人集”,名为《当代文化艺神》,出版社在样稿上注了小字:“若欲与刘大为、沈鹏、范增先生合著,可在回执单上注明。”
对于名满天下的黄永玉和范增,老刘自然是羡慕的:他们已经是大名人了,根本不必在乎“荣誉证书”,一幅画就能卖出大价钱;而自己,只能先通过“获奖”挣名气,再图利益。
老刘的一大愿望,是自己的作品,能够进入艺术品市场。
他最近收到的信中,有一封是来自“中国商界精英俱乐部”的,号称能“收购并拍卖当代书画作品”,只要付150元的“通联费”,便能将老刘注册为特别会员,让他的作品“上网拍卖”。
“就算是受骗,也花钱不多。”老刘决定再赌一回。前几天,“俱乐部”打电话来,问老刘那张四尺长的“墨宝”起拍价定多少,老刘一高兴,回答说:“8000。”
再一次,老刘心怀期待——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卖掉。
而一封封“荣誉信”,还在不断地往老刘家寄去。(记者孔令君 实习生郭妍 陈怡璇)
(来源:解放日报)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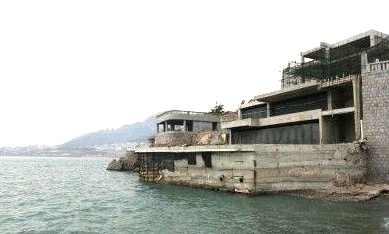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
发表成功!请登录后尽快修改密码。